【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添加微信好友, 获取更多信息
复制微信号
每年2.14这个日子,亲密关系总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如果要找一个世界级的作家来代言千禧一代的情感模式、立场和态度,1991年出生的爱尔兰女作家萨利·鲁尼(Sally Rooney)或许有这个资格,她也可能是其中最贴心的一位。从处女作《聊天记录》到《正常人》,再到疫情时期写就的《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这位青春当道、形象靓丽符合当代审美的女作家完成了她的三部长篇小说,也可能不少读者是从英剧《聊天记录》和《正常人》中了解这位文学界的青春偶像的。鲁尼的小说中,有大段大段的社交网络的原生态呈现,读她的小说,就像是在看这个时代社交网络的纪录片。她笔下的人物们一次次地看向手机屏幕,依靠即时通信系统保持联系;他们之间的聊天记录和通信被大量编织进鲁尼的叙事中。

萨利·鲁尼
在鲁尼看来,他们这一整代人都是失败的。从前他们这个年纪的人已经结婚生子偷情了,而如今大家到了三十岁仍然单身,和从来见不着面的室友合租。他们与父母辈有隔阂,相爱却互不理解。他们的生活围绕的是另外一些中心词:网络、手机、社交软件、聊天群、酒吧、派对、耳机、照片……他们的生活模式开始从线下朝线上倾斜,我们可以看到——回归私人生活、亲密关系和更小格局的“小确幸”,是千禧一代再自然不过的价值取向。
鲁尼2018年出版的《正常人》是三部中最优秀、最有深度的一部,入围了布克奖等数个国际奖项,这是一部“密室里的小说”。小说中提到男主角康奈尔“希望自己知道别人私下里是怎么生活的,这样他就能模仿他们”,当然读者的想知道并不一定为了模仿,而是为了去触摸生活中最细的褶皱。
在我看来,《正常人》是一部“私密感”呈现得特别显著饱满的当代小说,有着鲜明的90后代际征候。我这里说的“私密感”,也指人与人之间那种最赤诚的私密状态的直接呈现,是相对于公共空间里的社会人的状态。在过去的小说里,我们其实很少读到能真正深入人物最私密空间的小说“镜头”。在最为私密的空间里,人物如何思,如何想,如何行动。这是剥去了公共伪装后的真实的人类景观,鲁尼在这一点上,做得特别细致入微,有如手术刀一般精准。就像女大学生玛丽安对她一直爱着的男大学生康奈尔的真实感受: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和另一个人感到如此亲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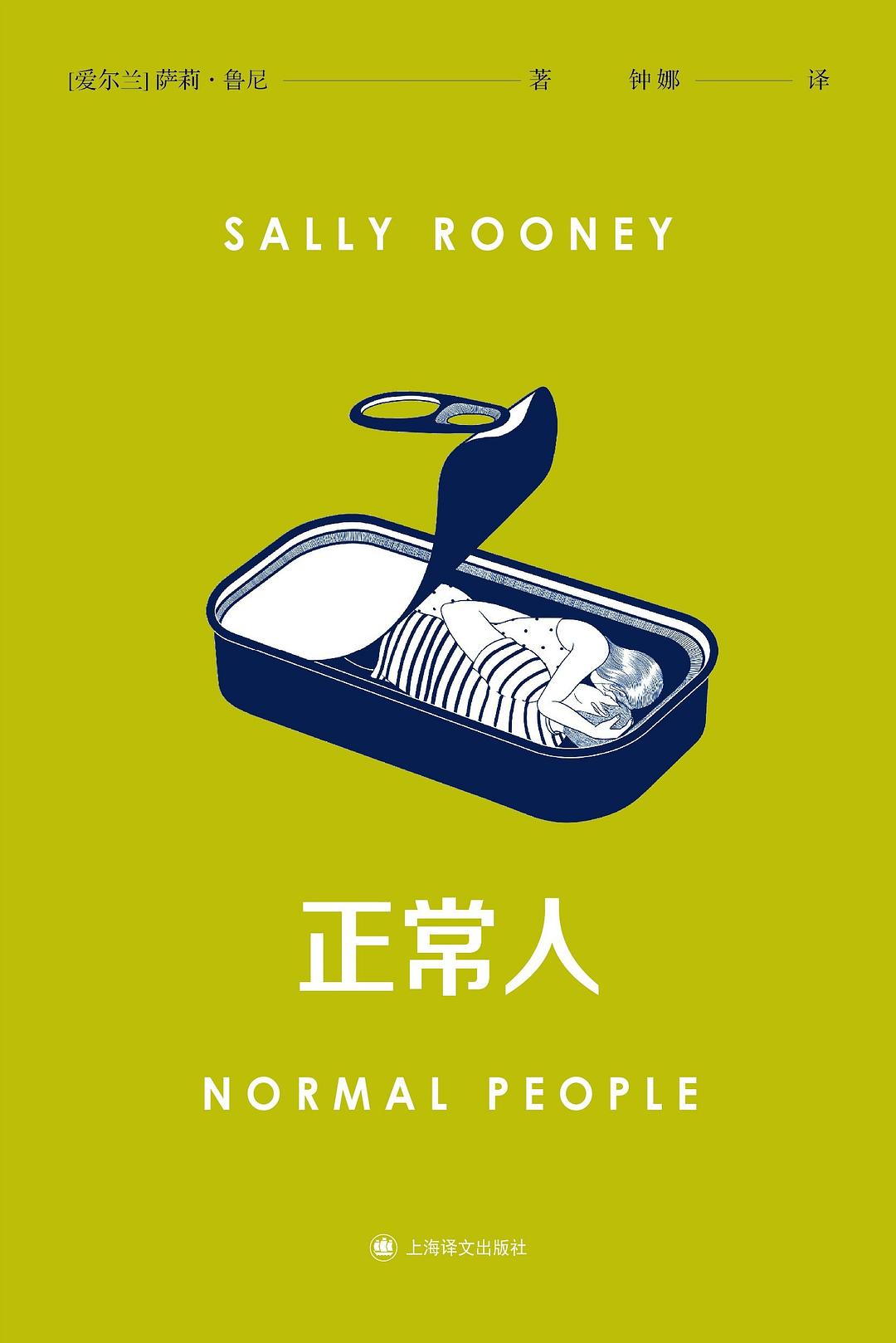
《正常人》,萨利·鲁尼著,钟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
我们每一个人在私密状态下,与在公众面前呈现的那个个体或许是有巨大差异的。文学一旦涉入这个“禁区”,就打开了另一幅更为隐秘的私人图景。就像白天与黑夜的区别。萨丽·鲁尼让这种物理性、动物性、复杂微妙的情感意义上的私密感充分呈现了,这个区域在《正常人》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时有惊人之笔。比如玛丽安与康奈尔之间的身体性、亲密关系和权力关系中的微妙变化,都只有在打开这个最私密的区域后,才能充分让读者看见并领悟到。这里面产生的文学力量是惊心动魄的,在我看来,不亚于一场《战争与和平》或《静静的顿河》中的战争,因为这是人的“内部之战”。这也是萨利·鲁尼之所以成为萨利·鲁尼的重要能力。
亲密关系是最小单元的关系。鲁尼说过,“在我的所有书的故事里,情欲是一个巨大的引擎。”还有一句话:“这并不意味着角色们总是想立即上床,但在很多关系中,驱动力是情欲的张力或欲望。”玛丽安与康奈尔,在他们的“密室”,人的多面性、立体感如此丰富,他们以极其私密的方式达到了身体性与精神性的双重联结;而在公共空间,同时认识他们两个人的人们既看不到这种复杂性,又能猜测到他们之间的隐秘关联。小说中关于两人的性爱描写无一处闲笔,鲁尼不为性而性,她写出的是人性中最危险的,也是最幽暗的部分,从而合乎逻辑地上升到亲密关系中的两个人的权力关系,但鲁尼最终抵达的,是亲密关系中被爱照亮和温暖的地方。在鲁尼的三部长篇中,这一特点都是鲜明的。她有超乎她年龄的深刻。我们在中国的一些90后作家的短篇小说中,也看到了这种倾向,但要说深刻与细致的程度,从我看到的小说来说,似乎还没有超越鲁尼的。
《正常人》中的私密区域还体现在玛丽安与艾伦的兄妹关系中。哥哥出于对天才妹妹的嫉妒实施长期霸凌、家暴,造成的伤害是在暗处的,是第三人无法看见的,兄妹俩的母亲则选择视而不见,事实上这位偏心的母亲已经成为哥哥的帮凶,一起对玛丽安实施精神伤害,让后者觉得自己一文不值,是个垃圾。直到玛丽安在再一次遭严重家暴后求助于康奈尔,康奈尔才发现了这一真相,从而也明白了玛丽安为什么会形成一种“受虐者”人格,这位看起来家境富裕、体面又聪明的学霸其实一直生活在不正常的亲人暴力和人格被贬低的阴影之下。她和康奈尔一样,是一个“穷人”。
在鲁尼的三部长篇小说中,社会关系、社会身份也一直占有很高的权重。鲁尼主要是从同代青年人的社交生活来展现这一点:长篇小说《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女主人公、作家艾丽丝在交友软件上认识了男青年费利克斯,费利克斯在“见到”她以前,已经在社交网络上搜索过艾丽丝的名字。艾丽丝在写给闺蜜艾琳的信中说:“哪怕只有一点社交都和完全没有社交截然不同——两周一次聚餐和完全不聚餐是截然不同的。无论e人还是i人,千禧一代对社交生活仍是重视的,再清高的人也不能完全撇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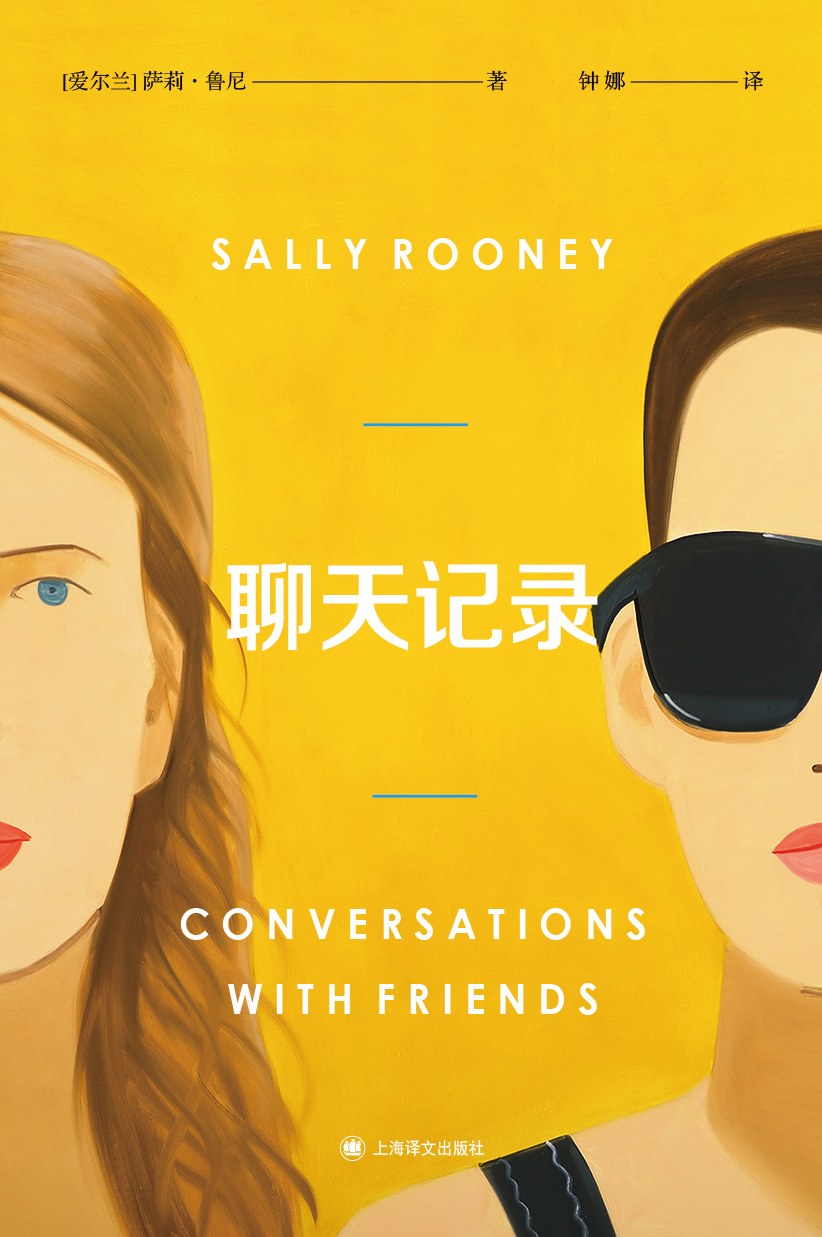
《聊天记录》,萨利·鲁尼著,钟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
《聊天记录》和《正常人》中,我们比较明显地看到,“他们的社交生活是分等级的,有人在最顶层,有人在中间挤挤搡搡,其他人在底下,而每个人都要假装对此浑然不觉。”人们似乎都知道社交生活的虚伪性,但又离不开它。《正常人》中,社交场域是玛丽安和康奈尔高中时期生活的爱尔兰西北部小镇卡里克里,后来是上大学的都柏林。
鲁尼写爱尔兰小镇:“卡里克里没什么地方能让一个落单的人不那么显眼。她没法一个人喝酒,也没法在主街上买咖啡。到最后甚至去超市也不行。”这就是一个熟人社会的小镇社交场域。在这里,不合群者就像是孤独的怪物,这种氛围会给人造成无形的精神压力,更何况是像玛丽安和康奈尔这样过于敏感的心灵。在《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里,青年人的社交也是如此,派对动物们有一个合理的闭环。孤独的女作家艾丽丝因为孤寂,也贸然参加了工人阶级出身的费利克斯的派对,渴望融入。
在《正常人》中,男女主人公的高中时代,恰恰成人化的社会阶层那一套还没有进入校园法则。康奈尔的母亲洛兰是玛丽安家的清洁工,所以洛兰对儿子说:“我认为她可能会觉得我们跟她不是一个阶层的。”但在高中阶段,这一身份差异的影响并不明显。康奈尔是校园明星,因为相貌英朗性格阳光体育好成绩好而大受欢迎,玛丽安却因为性格古怪疏离,没有一个朋友,他们在校园社会闭环里,身份不平等,玛丽安处于低处,康奈尔在高处,康奈尔明明已经与玛丽安有了性爱关系,却假装和玛丽安很疏远,玛丽安也默认了这一点,但康奈尔在毕业舞会上选择了欺辱过玛丽安的女生作为舞伴,很深地伤害了玛丽安。高中时期的康奈尔是软弱的,他屈服于校园“社交法则”,受困于高中圈子化的社会环境做出了势利的行为。这种“校园名人”的光环,使康奈尔套上了身份的枷锁,导致两人第一次分手。

萨利·鲁尼
鲁尼指出,青年人为了逃避孤独,在相对固化的社交生活中是容易迷失自己的。鲁尼笔下的爱尔兰小镇青年们,露骨地交换着彼此的社交资本,以使自己在社交场立足。康奈尔和玛丽安的高中校友罗布曾做出很不正确的行为:他为了更受人欢迎,给同学们看手机上保存的自己女友的裸照。但正是这个行为很“渣”的罗布,后来死于自杀,这表明罗布有自己不为人知的迷茫和痛苦。他是否反思过“卖女友求荣”的往事呢?小说里罗布自杀后,镇上的朋友们谈到他——
“一月的葬礼上,人人都在说罗布有多好,是多么充满活力,多么孝顺等等。但他也是个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人,为了受欢迎而鬼迷心窍,因为绝望而不择手段。”
孤独的玛丽安也曾屈服于“社交”,“她察觉到自己在社交圈子里渐渐站不稳脚跟”,她会为此而焦虑。或许在我们女性成长的过程中,很多人也曾像玛丽安那样因为被孤立而焦虑过,为了获得友情而低自尊,就像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她明白,中学里的男生们试图用残忍和冷落来攻陷她,大学里的男人们试图用性爱和追捧,都是出于同一种目的:“制服她性格中的某种力量”。玛丽安感到愤懑,自己竟然被他们蒙蔽,竟以为她和他们有共同之处,竟然参与交易过他们兜售的友谊。为了显得合群而做傻事,在对自己并非善意而有强烈掌控欲的女友佩吉面前步步退让,对方以“我是你最好的朋友”行自私自利之实,玛丽安为了保住友情,甚至到了毫无原则的地步——“和佩吉的角力是一场苦战。”
鲁尼在小说中很生动地以一个个切面,揭示了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社会身份、社交生活对当代青年人的影响。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原子”,都在尽力避免成为孤岛,为此不惜让渡自己的权利,去讨好他人。而在小说的前几章里,玛丽安独狼式的生存也自有她的困境和艰辛。
由此,《正常人》从私密关系与群体关系两个镜面,单刀直入,进一步探讨了亲密关系中的权力边界问题。人是否可以在关系中让渡自己的自主权,安心地做一个被掌控者?这种所谓的幸福是真实的幸福,还是被催眠的幸福?爱情中的权力边界又在哪里?小说最后两章可能让女性读者感觉不适,因为玛丽安似乎让渡了自己,臣服于康奈尔,甘心让康奈尔掌控她,而康奈尔也知道这一点:他可以掌控玛丽安,他让她做什么她就会做什么。小说中写道:“他可以让她自愿屈服,无须诉诸暴力。这一切似乎发生在她的人格深处。”那么玛丽安在小说的最终,康奈尔虽然从哥哥的暴力阴影中拯救了她,但并没有使她真正成为“正常人”,长期的受虐使玛丽安主动需要在性爱关系中变成“SM”中的那个“M”。相信很多读者和我一样,读到这里是悲哀的,甚至会怪作者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不还玛丽安一个正常人的独立人格?但我深想了几想,比起刚刚得到救赎的玛丽安马上变成“正常人”,玛丽安精神上更需要的,或许是康奈尔对她人格的接纳,对“不正常”和“受虐者”人格的接纳,他们之间,可以因为彼此接纳而相爱。事实上,在成长过程中,玛丽安同样也是抑郁到想要自杀的康奈尔的救助者,她帮助了他。从这一点上,他们是平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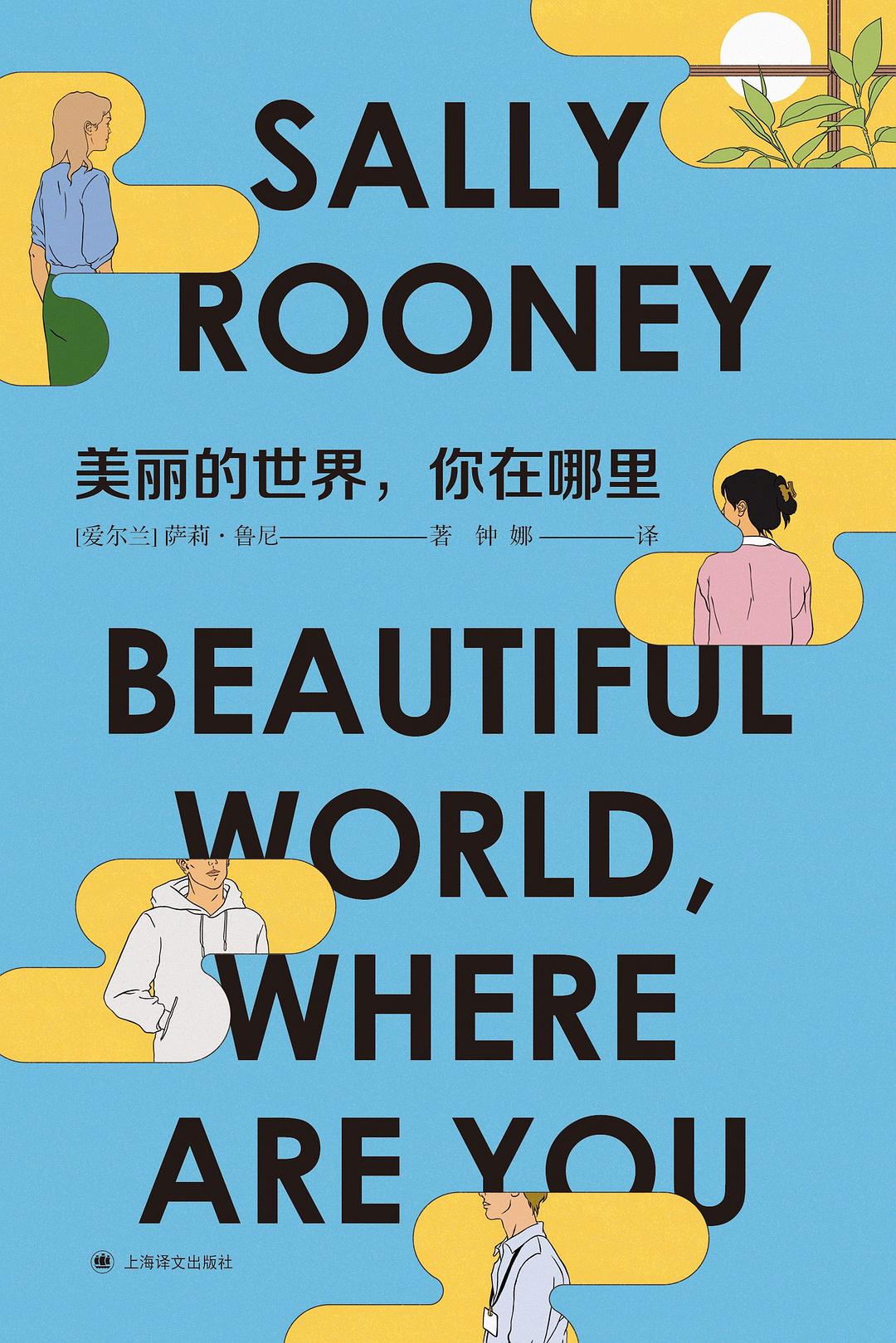
《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萨利·鲁尼著,钟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
同样的议题,在最新的长篇小说《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出现。女主人公、作家艾丽丝有严重自我怀疑的人格障碍。之前她住过医院。没什么朋友,亲密关系紧张。男主费利克斯对艾丽丝的人格分析:他认为她想通过他来伤害自己,但他恰恰不是那个她选中的去伤害她的男人。他用爱和温暖颠覆了她的认知。
作者鲁尼或许是矛盾的。在她的小说中,鲁尼借玛丽安之口有诸多输出。一个观点是:暴行不仅会伤害受害者,也会伤害施害者,或许对施害者伤得更深、更持久。我认为才三十出头的鲁尼有些天真了,这个观点或许只对心存善良的人奏效,对世界上极少部分的真正的“恶魔”,他们并不会去真正反思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鲁尼的另一个观点是:没有人能完全独立于他人,何不干脆放弃这种尝试呢?
这或许可以说,是三十岁出头的青年作家鲁尼的理想主义,在这样的理想主义中,还有几分女性特有的柔情。这种理想本身既可能是高贵的,同时也可能是脆弱的,这取决于人生存的环境,是相对阳光有爱的,还是穷凶极恶的。起码在玛丽安原生家庭的小世界里,鲁尼的梦就破碎了。
再往下说,就是人到底要如何构建自己,鲁尼书中的年轻大学生们,可能前一秒自命不凡,后一秒又低声下气。《正常人》中出身富裕家庭的玛丽安,一个缺爱的、高敏感的、天才又孤独的女孩行走于人群、社会,险境丛生,惊心动魄。因为长期在扭曲的家庭中成长,其实有破碎的自我,被打碎的低自尊,她是自卑的,觉得自己不配得到爱的。“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坏人,应当被人虐待”。而康奈尔是私生子,底层工人阶级家庭,贫穷是他的困境,在圣三一大学,出身底层成了康奈尔的自卑。他们在大学期间的分手,完全是源于康奈尔与玛丽安的阶层和贫富差异,一个说不出口自己的经济困境,一个体谅不到那个点,两人因误会而分手。在中产阶级出身的学生云集的大学,康奈尔在社交生活中不再突出闪光,也因此发现了社交的虚无,他找到了另一条路径:好好学习,读书,开始写小说,发现自我的更多可能性,获得纽约创意写作硕士项目录取,康奈尔是因为玛丽安的建议而选择了文学,放弃了法律,外部世界向他重新打开了,他也获得了构建未来的新希望。
玛丽安是如何重建自己的?自打孩提时代起,她的人生就不正常。关于玛丽安的“不正常”人格,我们看到作者鲁尼的态度是复杂的。她借康奈尔之口,指出了玛丽安“身上有让人害怕的地方,在她的灵魂深处有某种巨大的虚无,就好像你在等电梯,结果门打开时里面空荡荡,只有漆黑的电梯通道,永无尽头”。这一笔是幽暗的。小说又提到玛丽安在瑞典时的感受,一种虚无感,仿佛她的体内空空荡荡,没有生命。她痛恨自己,却无力改变。
鲁尼在小说中埋下了几处伏笔,小说中有玛丽安和男友杰米相处时期,要杰米打她,她关于“服从性测试”的自白,她认为自己并没有真正去服从,后来她主动对杰米说不,两人分手。之后,在玛丽安去瑞典当交换生时期,瑞典男友要拍下她“性受虐者”角色扮演的照片,但渐渐地玛丽安觉得不妥了,即便已经双手和眼睛被缚,她也激烈反抗,坚决说不,不然就要报警。在后来她跟康奈尔的性关系中,她也要康奈尔打她,但康奈尔拒绝了,这让玛丽安伤心,因为她认为她的“不正常”没有被康奈尔接纳,她认为康奈尔觉得她是恶心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玛丽安在这种SM游戏中,她说“不”就是“不”,这说明玛丽安的自我依然坚实地在那里,她并不懦弱。那么是否可以认为,玛丽安依然是自己在掌控自己的性权力,她在让渡自己的性权力时是有选择的。她可以把权力让渡给她真正爱的康奈尔,是出于她对康奈尔的正直人品的了解、信任和安全感。一旦感觉到危机,玛丽安随时可以收回这种权力。在《正常人》中,鲁尼对性与权力的关系的深入探讨是可信的,这是小说非常有理性有力量的部分。

根据萨利·鲁尼同名小说改编的BBC剧集《正常人》海报
作者在最后描述康奈尔得到了纽约深造的机会,玛丽安为成全他的梦想,鼓励他去纽约继续深造,她说:“你去吧。我会一直在这儿。”玛丽安的内心:“孤独的痛苦远比不上她曾经的痛苦,那种觉得自己一文不值的痛苦。他将美德赠给了她,现在它是她的东西了。”
我们也可以认为鲁尼在写作《正常人》中,是偏向于女性主义的写作。性话题延伸的恶意总是无处不在,针对女性的恶意常常更多,而且常常无中生有。“一次派对上,一个喝醉了的男人跟他说玛丽安有奇怪的癖好,网上有她的照片。”荡妇羞辱总是屡试不爽,似乎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女性一不小心就成了他人传言中的妓女、婊子、荡妇。鲁尼在书中指出,男人们掌控了整个社会关系,即便已经是在一个网络时代。玛丽安在两性关系中,总是要比男性承受更多:比如与杰米分手后,她遭受的流言,对女性实施的荡妇羞辱,羞辱像裹尸布一般将她包裹。同样如果反过来,男性几乎不怎么受伤害,性羞辱对男性几乎是无效的。鲁尼借玛丽安和康奈尔的讨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哪怕到了当下,女性相比男性依然要面对的性别困境——
“我认为这是个名誉损害的问题。
那为什么杰米的名誉没有受到损害?康奈尔问,是他在对你做这些事。
对男人来说不一样,她说。
嗯,我也意识到了。”
鲁尼的女生主义立场也时时出现在第三部《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一次和费利克斯交往中,费利克斯的手机里弹出黄色网站的图片,艾丽丝看到后感到十分不适,当费利克斯说“还有可能你嫉妒她们”时,艾丽丝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自己的抗议。
最后我要说的是,当我们已经走过步步惊心的青年时期,看鲁尼的三部曲里充斥着酒精——一个爱尔兰小镇的酒吧或许就是一个社交中心,《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开篇第一句:一个女人坐在一家酒店的酒吧里,注视着门口;《正常人》、《聊天记录》里,派对上的男男女女们都去那里喝酒,度过感恩节圣诞节或生日等重要节日;主人公们时常有喝得烂醉的描写——会像个长辈那样有些许担忧,这样的生活方式潜伏着危机。《正常人》中,玛丽安曾在一个派对上被女朋友诱惑吸了大半条可卡因,还吸过一次大麻,还有数次醉酒。康奈尔也有数次醉酒。另两部长篇中的主人公也有酒精问题。但回想我们自己的青年时期,也曾在一场一场的宿醉中确立自己的存在,也曾颠三倒四地迷茫地生活在危险丛生的探索中,我们也就释然了鲁尼三部长篇小说的酒精浓度。爱尔兰人生活在高纬度的岛国,想起爱尔兰咖啡是加酒精的,爱尔兰巧克力里也有酒心巧克力的,青年时期,人生有时就是大醉一场,有时则是冒险地大爱一场。而中年人,最终都越来越趋向于保守主义,我们在90后的鲁尼身上也发现了这种苗头。但对一个敏感的年轻人来说,成长过程中真正的社会性危险在哪里,边界在哪里,如何才能保护自己?或许正是鲁尼这部小说想尝试的一个命题。
萨利·鲁尼的“小世界”,在互联网和酒精、性爱之外,是过于敏感的心灵,是渴望爱的青春与灵魂。在阅读鲁尼时,我们会渐渐习惯鲁尼的风格化写作:虽然她的小说中有大量日常化描写,但这些描写也是属于网络时代的场景,是时时处处的网络化生存的生态,你很少能看到鲁尼让人物置身于大自然,置身于风、花、雪、月之间的描写,就像他们开车去某地的路上,也许不是在看窗外的风景,而是在低头玩手机。这就是这一代人的基本生态。这也是鲁尼小说独特的“网红气质”。这也提醒着我们,当一代人已经不太能够从大自然中获得心灵安慰时,孤独的灵魂又将如何安放?人与人之间又将如何相处,如何建立亲密关系?这是个重大课题。
“或许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去爱我们认识的人,为他们担忧,哪怕本应做更重要的事。如果人类会因此灭绝,这个理由难道不够美好,难道不是你能想得到的最好的理由?当我们本该重组世界的资源分配、一起过渡到一个更可持续的经济模式时,我们反倒在关心性和友谊。因为我们太爱彼此,觉得彼此太有趣。 ”这似乎是鲁尼的时代宣言。
鲁尼式的“乌托邦”始终贯穿于她的三部长篇小说中。她有对理想社会生态的看法,比如她对资本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但同时她也借书中人物之口,反思“什么事都和资本主义有关,这才是问题所在”。她的三部小说都想去打破阶级差异,让不同阶层的男女之间相爱,展开爱情和友情。《正常人》中,玛丽安的父母都是律师,而康奈尔的母亲是17岁怀孕辍学生子的清洁工。《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鲁尼让因写作而富有的女作家艾丽丝爱上了超市工人费利克斯,并试图以两个人的互相了解,一步步走近成为知心人,去填平阶级和贫富的鸿沟,小说结束时两人还在热恋中。她的三部小说的主人公们都关注政治,关心地缘政治文化冲突,会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三部小说中常见的场景有文学活动、戏剧沙龙和知识分子们的高谈阔论,主人公们穿梭其中,不时表达自己的观点。三部小说中都有主要人物成为了作家,都有爱尔兰青年知识分子的文学生活场景:作品分享会、朗读会、文学刊物编辑工作等等。这一点,让人想起了她的前辈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依斯的《都柏林人》和《青年艺术家的肖像》。这些都显露了鲁尼小说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气质。
在《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以及她的处女作《聊天记录》中,鲁尼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人还是需要友情、爱情这些情感和关系的,在人与人的亲密关系中彼此支撑着,才能真正美好地生活在世界上,她并不只强调独立的意义。在《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的最后,鲁尼借艾丽丝的闺蜜艾琳之口,说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我大概觉得孕育一个小孩是我能想象自己做的最平凡的事了。我想要完成这件事——来证明人类最平凡的品质不是暴力或贪婪,而是爱与关怀。她曾经姿态先锋,现在过了30岁就回归传统价值观了?并且给出了类似大团圆结局,敏锐的社会批判让位于爱的呼唤,鲁尼变了吗?这或许是这部疫情时期写作的长篇引发争议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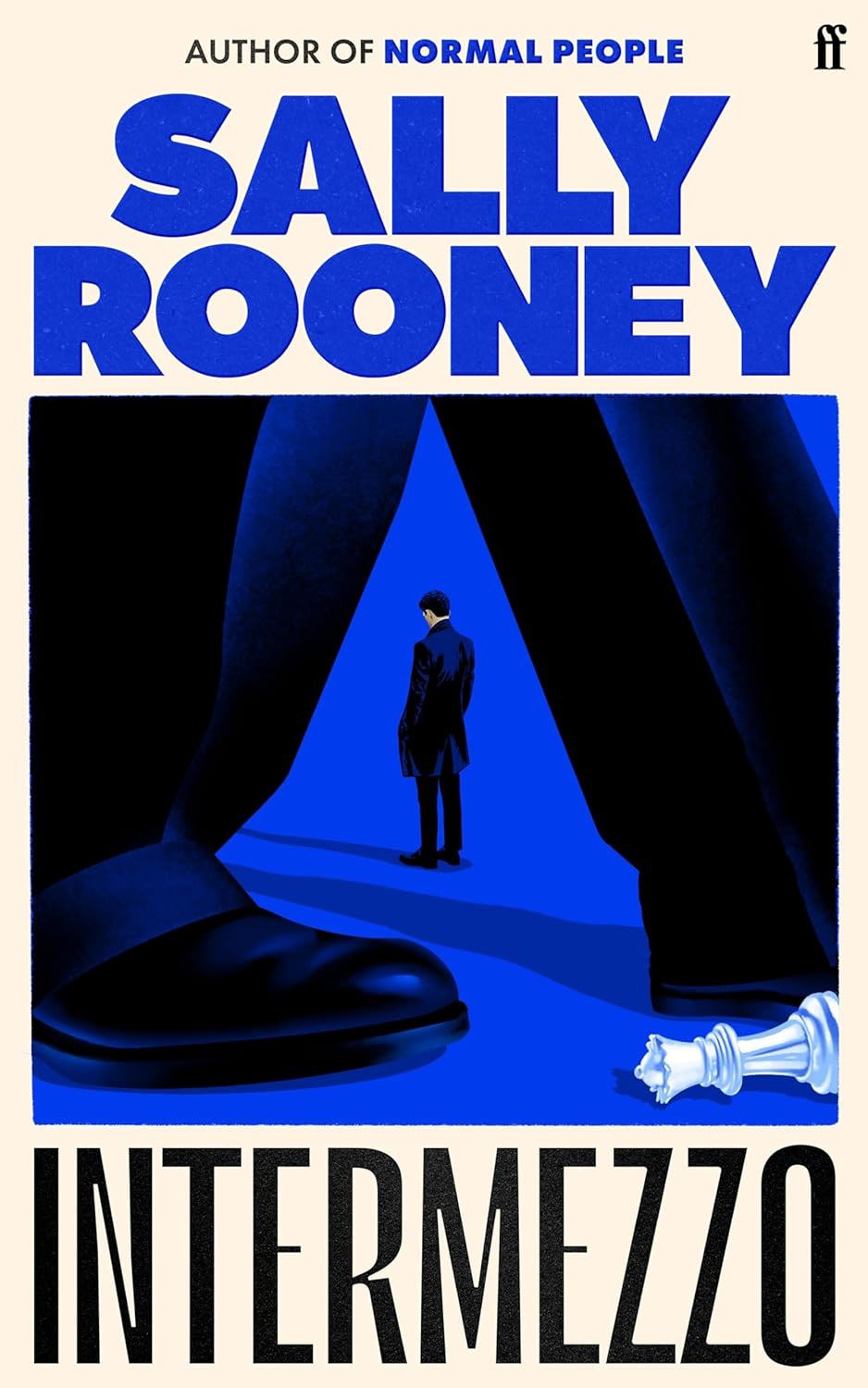
Sally Rooney(2024). Intermezzo. Faber & Faber.
顺便说一句,萨利·鲁尼刚出版的最新作品《间奏曲》(Intermezzo),故事围绕一对中产阶级兄弟展开,其中主要人物依然被社交障碍困扰,依然是爱情与成长主题。《间奏曲》中译本有望在今年春夏在中国出版。
(萧耳,作家,浙江工商大学金收获写作中心副主任、特聘教授)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