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多和田叶子,1960年生于东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系。她是芥川奖、谷崎润一郎奖、泉镜花奖三满贯得主,有着“比村上春树更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女作家”“贝克特、乔伊斯和卡夫卡的当代精神传人”等美誉。“反乌托邦”末世小说《献灯使》是她的最新中译本作品,以超绝的想象、绮丽的语言,构建了一个充满荒诞、希望和爱的末日世界。
添加微信好友, 获取更多信息
复制微信号
多和田叶子说:“耕耘语言,捡拾语言,用镰刀收割语言。”这似乎是她写作的信条。在她新近出版的于2018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小说集《献灯使》的中译本里,作者的黑白照片出现在书页的左下方。她留着简单的短发,丝质围巾在肩颈处交叉缠绕,向后滑落肩膀,眼睛望向斜前方,嘴角挂着高深莫测的笑,因为是黑白照片,衣服颜色无法辨认,但总觉得是魑魅的黑,包裹着她狡黠幽森的气质,她果然像是调配语言的女巫。

《献灯使》中作者多和田叶子像
她叫我想起深海,《海的女儿》里那自开篇伊始所描绘的蓝得“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深得“任何铁锚都达不到底”的深海,她是蛰伏在深海再深处的那个留着蓬松鬈发的女巫,用蟾蜍和水蛇来调配药汁,嘴唇哈出热气,她有那种波动周遭涟漪的能力,当她开始煎煮药汁时,珊瑚虫和水草蠢蠢欲动。一切不过是为了让火势更为浩大。她说要收割语言,于是她诱惑小美人鱼割下舌头——她的嗓音、她的语言,然后把它投进滚烫的药中,她说,要让药变得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子。药,也是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对文字的隐喻:兼具“解药”与“毒药”的双重性。
作为一名痴迷于制造语言游戏和文本巫术的作者,多和田叶子的小说常被纳入“反乌托邦”写作的脉络。归纳总是容易,如同给开架商品贴上千篇一律的标签。可就像“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特定的颜色不过是渐变过渡的光谱,瞬间捕捉到的“相”也不过是万花筒恰巧转到某一角度的碎片,定义下的主体,自有其跑马的疆域。
如若说,陈列在“反乌托邦”文学里的那些经典们,叶甫盖尼·扎米亚京的《我们》,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场》,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都自有其手术刀尖锐的所指,《我们》和《1984》指向全景监视的极权,《动物农场》指向谎言的编织与散布,《美丽新世界》指向科学技术对人的全面定制和操控,多和田叶子的《献灯使》相较而言,并没有那么深刻和锋利,它有日式小说独有的轻和缥缈,更像是一场企图渗透你的烟雾,漫画式的妖冶华丽,袅袅荡荡,它讲语言的变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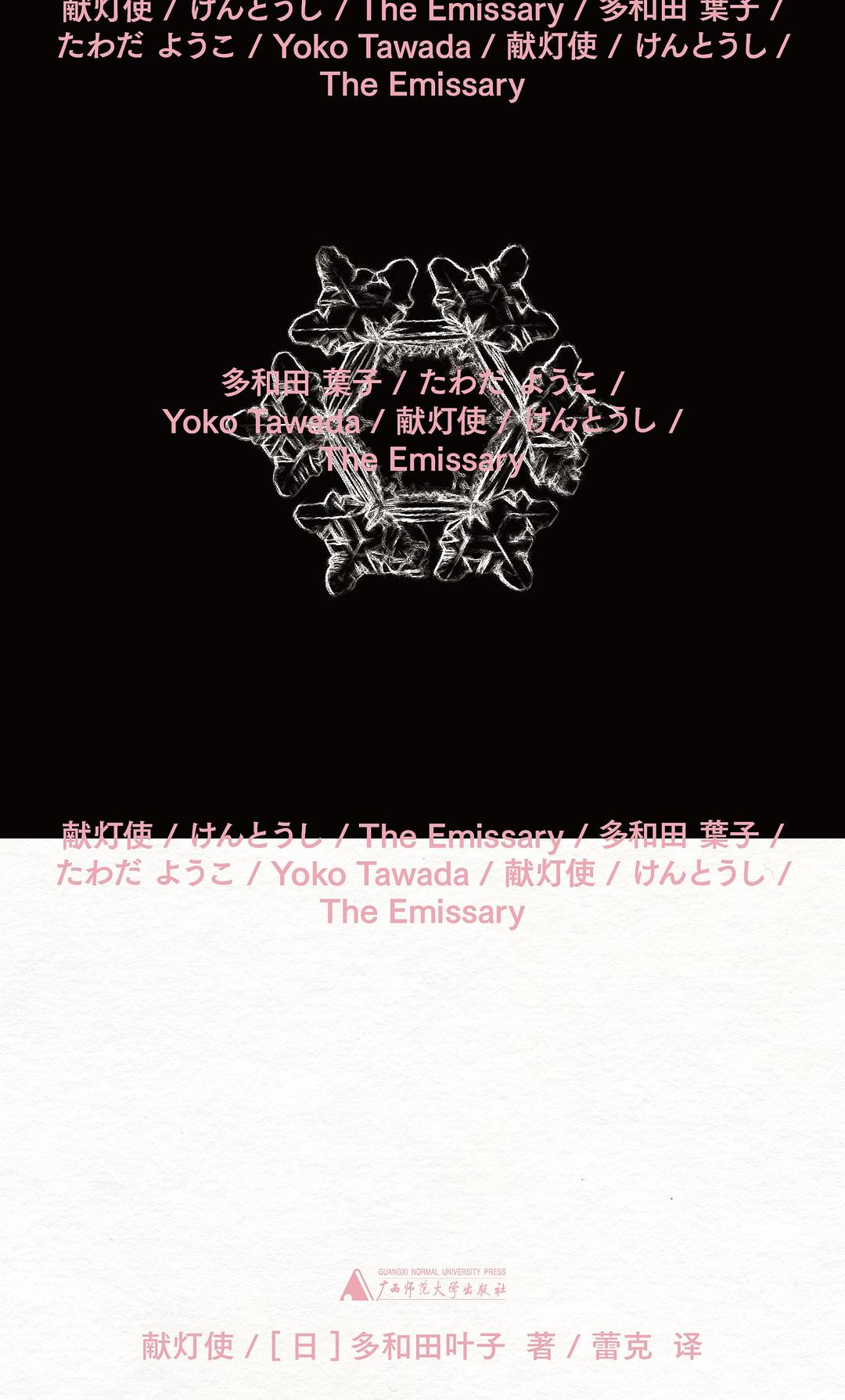
《献灯使》,多和田叶子著,蕾克译,野spring×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272页,65.00元,精装。
整部小说集由《不死岛》《献灯使》《韦驮天踏破一切》《彼岸》《动物的巴别塔》五篇作品组成,其中《动物的巴别塔》是部舞台剧,其它四篇均为小说。五篇作品看似独立,但实际上又相互勾连,在气质上一脉相通,仿佛从拼图的不同侧面,暗合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的迷幻轮廓。
故事设置在2011年日本福岛大地震核泄漏事件之后,作者将现实和科幻并置在一起,甚至让你觉得,她试图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口吻引诱你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以至于让你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诡异的“恐怖谷”效应:到底是科幻模拟了现实,还是世界变化太快,以至于现实已追赶上了科幻?
语言变形的初始是物的变形。在作者的描绘下,日本由于核辐射污染而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本就远离大陆的日本岛更加向大海深处漂移,孤独成为常态。核辐射导致年长之人拥有不死之身,永远长寿,初生的儿童在他人的悉心看护下才得以苟延残喘,但生命脆弱如同空心芦苇,说不定哪一天就随风而逝。没有电脑,只剩用太阳能电池驱动的小型游戏机,最近在市场上流行的,是从能剧中获得灵感的《梦幻能游戏》,游戏的主角是含恨而死的人,话未说出口便化为幽灵。
环境恶化,资源短缺,水果和蔬菜成为了稀缺物品,一枚圆圆的橙子,可媲美黄金。象征日本的菊花在世界范围内被污名化,这一花卉如果出现在护照上,更是不受入境官的待见,以至于因为恐惧,护照上的菊花花瓣会在幻觉中发生变异。突然变异增大的蒲公英,因为酷似菊花也连带受到歧视。为了平息民众的慌乱,官方宣称,从词汇库里消除“突然变异”这一词,而改为更为温和的“环境同化”。
崭新的语言开始重新命名事物。在《1984》的世界里,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负责造谣,友爱部负责拷打,富裕部负责挨饿,“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多和田叶子没那么犀利,她更诙谐更暧昧。在核辐射后的废墟世界里,为了切断锁国中的日本和外界的联系,大量外来语被禁止使用。小说中的孩子都由祖辈或祖祖辈抚养长大,为了弱化与父母之间的情感失联,“孤儿”改名为“独立儿童”,“敬老日”变成了“老人再接再厉日”,“儿童节”变为“向儿童道歉节”。“体育日”会让现在身心无法发育的儿童心碎,于是改成了“身体日”,“勤劳感谢日”为了不让想劳动却没有机会的年轻人伤心,改成了“只要活着就好日”。为了维护社会秩序,“逮捕”“嫌疑”等词汇也在悄无声息中消失不见。
多和田叶子创造了一个散发着诡谲气息的荒诞世界,一切都颠倒了过来,长与幼、贫与富、快与慢、男与女……它们在错乱的世界里流动变化,甚至朝令夕改,事物每天都因新语言的发明,而被赋予截然相反的涵义。新概念层出不穷,将话语的陷阱伪装成一口幽深的古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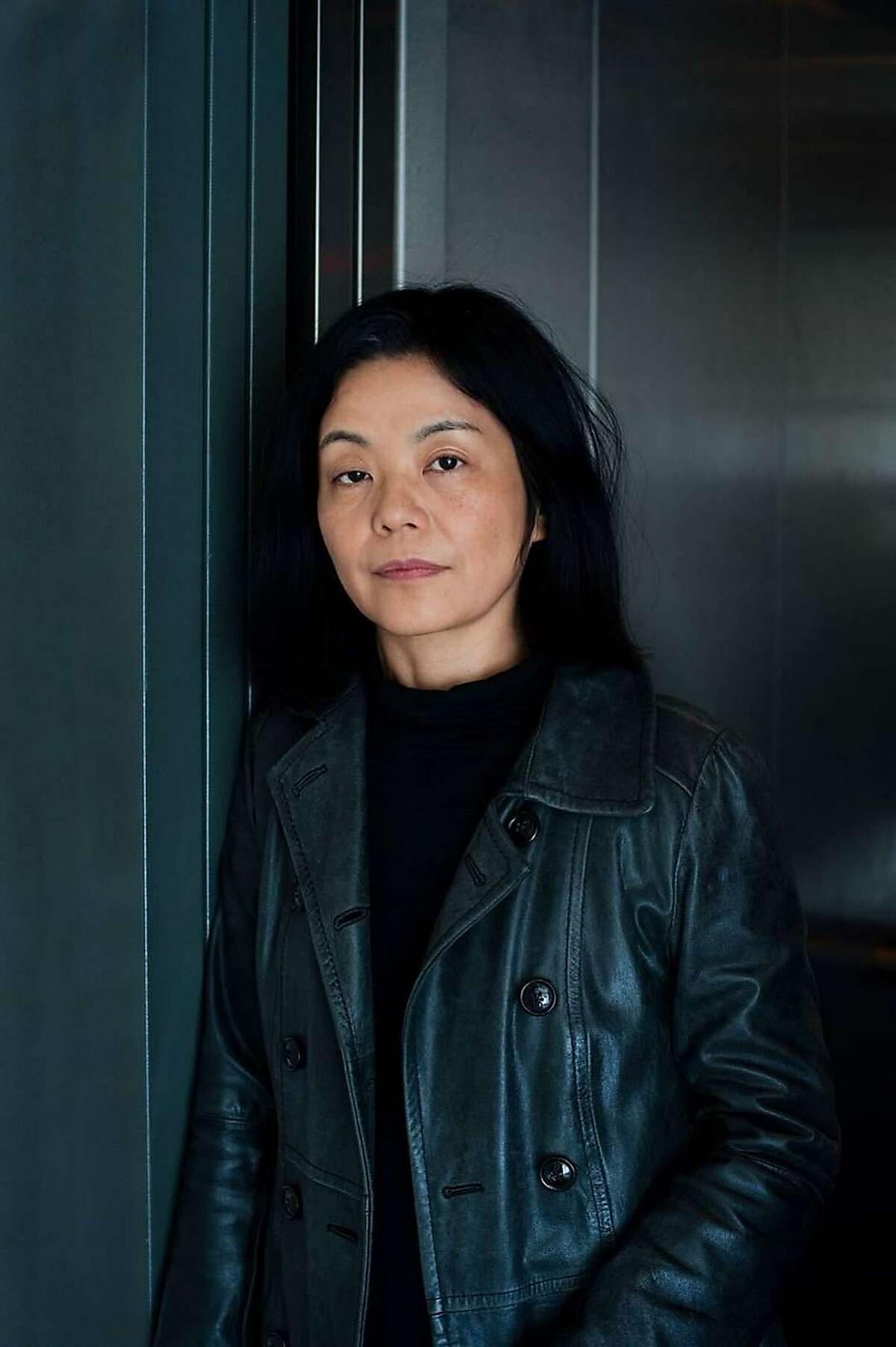
多和田叶子
维特根斯坦认为,“我语言的局限,即是我世界的局限”,不是我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思想的暴政从语言的暴政开始,像一件紧身衣,表面流光溢彩,但暗自塑造你的思维、你的性格、你的情感、你看待世界的方式。从天而降的定义和标签,可以展开污名化的围猎,语言的突然松绑,也可以对凶神恶煞的罪犯进行赦免。天使与魔鬼,在语辞的两端触手可及。
常识在堕落,但也让聪明的少年找到逃逸的出口。少年飞藻是童话里那个看到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他不爱学习,爷爷义郎担心他的未来,便送他一笔银行存款,充当综合职业学校三年的学费。他却早早将钱取出,偷偷离家出走浪迹天涯。没想到一个月后,多家银行连续倒闭,储户的存款一夜蒸发,飞藻却幸免于难。少年说他看穿了经济结构,他不相信银行,也不相信学校。他看到它们如多米诺骨牌般脆弱的组织,崩塌的大地让常识的天平激烈晃动——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善?是逼迫人们无视商业规律,纷纷被架上道德的高台,去扮演散尽千金的慈善家,还是尊重基本的经济规律,让经营者专注于经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效益?
多和田叶子不提供答案,我有时觉得,她似乎连读者也不在乎,她通过在文本中制造语言的核爆来展现核爆后的语言游戏,单纯的语言炼金术叫她着迷。有时,她仅仅为了搭建临时的语辞迷宫,而牺牲故事性,让人物充当筑砌这迷宫的砖瓦。这个时候,作者也成为了文本的暴君,人物被迫压缩了个性。
她的文字有一种悬浮的无根性,像烟花,一旦燃爆,就向四周扩散,每一朵逃逸的火星又能重新长出自己的枝丫,再度繁殖结网,然后她就会思考:是要在网上放生一只蜘蛛,还是滑落一颗冰冷的眼泪?
她不擅长在语言的某处深度停留,将人物的血肉塑造出来,而是一反逻辑地无规则滑行。她借“插花”写女人的情欲:“花朵有时会妖化成其他东西,比如有时草字头会消失不见。妖化之花很可怕。”完全是象形文字系统里才能玩的文字游戏,又如,她单靠“東田一子”和“束田十子”这两个字形互补的名字,就铺陈出一场女人之间的情感奇遇:“二人互相争夺,夺还,改变字形,改变笔画数,尽情享受着唯有汉字才能赋予的奇异快乐。到了后来,她们自己也分不清了,究竟谁是東田一子,谁是束田十子。”
情节和人物有如一支即兴的舞蹈,是水与火此一刻的化学反应,是仰天对着月亮说:“今朝有酒今朝醉。”小说世界也似瞬息万变的浮世绘,里面有如鹤的少年、在歌里吟唱蜻蜓的少女、想要变回蛸的男子、在稻田里看到落日的女人……不断变幻的浮动的世界,分明是一张张歌川广重的风景画,江中垂钓,梅下点灯,雪中望月,或是疲惫挑夫视角下的漫山早樱,为了展现樱花的烟云旖旎,原本筋骨分明的枝干反而幻化成为星星点点,到底谁是主,谁是客,谁是镜像,谁是生活的真实?
可是,就像极权的背阴面,总需要爱的弥合,来重新锚定重量,每一本“反乌托邦”的小说里,都存在一对纯真而叛逆的恋人。他们是《我们》中的D-503和I-330,《1984》里的温斯顿和裘莉亚,《美丽新世界》里的琳达和托马斯。《献灯使》里的无名和睡莲也在偷偷相爱,多和田叶子在书中写的最温柔的话,是森林里的兔子说的:
“不过,有时候被人类抚摸,是会很陶醉的。人类有种神秘的力量叫作厄洛斯——爱。人类抚摸包菜,包菜茁壮成长。人类亲吻花蕾,玫瑰会提前一天开放。”
“这是基因操作?”
“不是,是自然与人类之间的恋爱关系。”

《献灯使》立封
(本文作者系复旦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美学博士)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