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吴琦、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宝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冯贤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郑小悠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主办的“2024大学问年度学术出版论坛”上就“政治、文化与社会:多元视角下的明清史研究与写作”这一主题进行了对谈,主持嘉宾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敬雅。本文系对谈的文字整体稿。
添加微信好友, 获取更多信息
复制微信号

对谈现场
王敬雅:大家好,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王敬雅,很荣幸可以做今天下午圆桌会议的主持。
想请四位老师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是:明清时期的城市化进程逐步地改变了官绅和百姓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其实与相同时期的欧洲相比,我们的城市化进程要更充分,或者说更快——在这种城市化的进程中,普通人或者说是不普通的当时的官员、官绅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有哪些改变?请四位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吴琦:上午我的报告里面谈到商品经济,包括大运河与沿线城镇发展的问题。明清时期无论是商品经济还是城市化,在中国历史上都达到了一个高度,达到了一个高峰,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明清社会变迁的一个结果。而城市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明清社会的大变化、大发展。
以我过往的相关研究经验来看,明清社会群体在社会大变动中出现了几个显性的特点,这些显性特点与明清时期城市化、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关联。
比方说,社会群体分化与重组的加剧,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频繁等,促进了群体之间的剧烈互动。还有,就是社会精英向优势区域集中,陈宝良老师在上午报告中也讲到社会精英向优势区域转移的情况,即乡绅城居化的问题。我们站在更大的视野里看社会精英向优势区域转移的现象,所谓优势区域就是中心区域,或者经济发达的区域,或者文化繁荣的地区,精英群体向这些地区转移,便引发一系列群体性的新趋向。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中国古代有一种特殊身份的士人——高士,而与高士相关联的现象是高士情节和《高士图》。所谓高士是远离现世的人,他们表现出一种孤傲、高冷。
王敬雅:感觉魏晋时期比较多。
吴琦:魏晋高士颇具代表性,但明清时期的高士也很典型,王朝更迭、政治斗争形塑这一群体。我们曾经写过一篇关于《高士图》的文章,明代瓷器上的《高士图》。在明代,无论是官窑生产、定制的瓷器,还是民间私窑的瓷器,无不可以直接反映社会生活。以明代的景德镇瓷器为例,放在明朝276年的长时段里来看,前、中、后期有很大的变化,这和我们讲的城市化和商品经济有很大的关系。
明前期,我们看到景德镇瓷器上的《高士图》,反映的是空谷旷野、人迹罕至的场景。有很多题材,像携琴访友,等等,确实给人一种很脱俗、很高冷的场景,那是真高士。反映出士人出世或者遁世的取向。
明中期,《高士图》有了变化,仍然是在山野之中,但可以感受到里面的主人翁开始享受这种出世。比如说焚香抚琴,旁边还站着侍童,甚至于还出现了高士身着官员朝服的景象,但总体还是在世外的场景里面。
到了晚明,高士就彻底放飞了,自诩为世外的高士,开始隐居于城中了。在城市的场景里,四周站着侍妾,还有满门的食客,他仍然自诩是高士,有高士情节,但隐居在城市,并世俗化,里面的场景表现出浓郁的市井氛围。我想这和明代的城市化、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系。
总而言之,明清时期的城市化、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予中国社会的冲击、给予中国社会的触动是全方位的,甚至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

明天顺 青花携琴访友图梅瓶 故宫博物院
王敬雅:谢谢吴老师,吴老师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选题。说起《高士图》,我突然想到明朝末年在苏州特别流行的苏州画,看过一本书是《伪好物》,明朝末年苏州人特别喜欢流水线式地仿造宋元时期的画作并用来出售。这些好物还骗过乾隆,乾隆收到过的一些元画——进贡收上来的认定是元朝的画家画的画,其实是明朝的商品。今天讲到苏州和杭州,下面请老师们分享一下对城市化和百姓、世人生活的看法。
陈宝良:以苏州的城市生活为例,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生活随之得以改变,而“作伪”更是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苏州工匠的工艺相当精湛,在明清时期甚至流行这样一句俗语,即“苏州样、广州匠”。这里提到了“广州匠”,似乎广州工匠的手艺相当高,但在明朝并非如此。广州工匠的手艺趋于精湛,即“广作”的兴起主要是在清代。在明代,还是以苏州工匠为代表的“苏作”更为著名。我们讲明式家具,实际上就是以苏作为代表。因为当时苏州工匠的作品引领着整个时尚的潮流,所以导致很多作伪现象的出现。今天上午我曾经讲过,即代表苏州人生活样式的“苏意”一词,恰好引领了明朝人的生活。苏州人认为雅的,别的地方的人也认为是雅的;苏州人认为俗的,别的地方的人也认为是俗的。明朝出现了“时尚”这个词。袁宏道专门写了一篇题目叫《时尚》的文章,里面提到的有名工匠大多是苏州人。这些有名的工匠,制作的器物分别有铜器、漆器、陶瓷等,无不精美绝伦,甚至被张岱称为“吴中绝技”。
这种作假的风气,甚至影响到家谱的修纂,即出现了赝谱。明朝制作赝谱最有名的人叫袁铉。这个人专门替人做赝谱,也就是假的家谱。他制作的赝谱,可以把所有的世系脉络传承梳理得清清楚楚,完全看不出作假的样子。
所有这些,都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尤其以苏州这个城市最为突出。在明清两代,显然出现了一种社会变迁,即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明清两代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甚至中间出现了明清易代这么一个过程,相对来说显得较为复杂,但从近代化的历程来看,海内外学者大多在整体上将明清看成一体。
那么, 这个时期又有哪些变化?刚才吴琦老师说了很多,我记得他刚才说到了高士。从某种程度上说,高士就是隐居的隐士。过去真正的隐士,是在山野里隐居,远离城市的喧嚣,这样才称得上是高士。到了晚明,所谓的高士、隐士,同样开始发生了变化。晚明把隐居分为两种:大隐和小隐。大隐是在朝市,隐居在城里那些热闹的地方;只有小隐,才隐居于山林。这些高士本来应该心灵很通脱,不应该去追求一己的私利,好像什么都看开了,也即看破了红尘。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像我们的论坛主题所说,最后还是落入红尘。
冯贤亮:我个人的理解是城市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现代理解的城市本身的发展形态或扩张,这当然跟我们经常讲的近代化或现代化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另外一种城市化在我看来就是生活方式,乡村、市镇甚至城里的人趋向城市,到城市里生活、发展,这也是城市化。
晚明以来后一个层面的城市化是一股很大的潮流,影响到各个方面。因此,我们要追问为什么出现这么一种明显的趋势?为什么出现城市化,或者明代、清代的士人经常讲的城居化的态势?
我认为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地域开发进程的影响,不同的地方地域开发的形态、深度当然是不同的,商品经济比较活跃,各方面产业发展得比较充分,地域开发、人群的集聚、产业集中,对这方面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是相伴而生的商品经济的活跃,商品化程度比较高,城镇化的表现形态就更充分一点,特别是对普通人的影响很大。
最明显的是这样一个例子。从春秋战国以来,我国古代便将人群分四类:士、农、工、商。但我们好像突然发现,这个分法到了明清开始有点笼统、有点模糊。我们发现,到了明代后期,很多文人的笔下描述社会阶层的时候非常细。细到什么程度?我以前看过一个笔记,一个叫姚旅的文人写了一部《露书》,书里把城里谋生的人常态化地增加了十八类,梳头的是一类人,专门是服务行业的,就像现在的美容行业一样,还有挑担的、算命的,分得非常细,甚至流窜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盗匪也是一类,靠这个为生的,你不能说他不是一个职业人群,所以生活的样态非常之丰富。
二是刚才讲的直接应对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就像今天讲的一样,有中心城市、有小城市,还有周边的卫星城市,这些大小城市共同建构成城市群或者城市生活网络,在长江三角洲发育得比较充分。晚明是以苏州、杭州为中心,晚清就是以上海为中心,重新建构长三角所谓的城市生活群或者城市网络,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另一方面比较突出的,或者说跟传统相比有比较大的转型的,是1840年以后,鸦片战争带来的巨大影响。
比方说上海因为近代有租界,人群大量地集聚,发展到今天还是一个移民城市,是多元、包容的城市。而近郊的农民、普通百姓发现城市化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机会,因此一方面他们会到城里谋生,会迎合城市化、成为城市市民,但另一方面他们还保留着乡村社会的生活方式。上海最明显,因为有很多洋人来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中国人不一样,到中国来肯定不适应。他们喜欢吃牛肉、土豆、洋葱,所以周边城郊的农民非常聪明,他们能快速适应。
上海周边本来是以棉纺业为主,水稻种得不是很多,农民马上改变生产生活的方式,种洋葱、种土豆,很快适应城市生活的节奏,也因此他们可能获得的收益比传统种水稻和棉花等更多、更好,这是给他们带来的一种福利,也让外面的人,除了上海,除了杭州、苏州还有其他地方的人看到,好像江南地区的老百姓生活很好过,因为他们赚到的钱比其他地方的人多得多。所以有一句口号是当时人经常讲的:“到上海去!”
晚明时期的张岱讲过,苏州是个很好的地方,是很多人向往的人间乐土。前面我们讲到的王士性说:“苏州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苏州人以为俗者,则四方随而俗之。”张岱是浙江人,他说浙江人很没有骨气,觉得苏州人好的东西就拼命学,但苏州人很快就把你学到的东西淘汰了。张岱很哀叹浙江人跟不上这个节奏,这也是一种城市化、或者城居化生活带来的影响。
王敬雅:我们知道郑老师主要研究的方向是清代,郑老师也谈一谈,清代在我们看来文化上更严苛、更保守,它的市民文化怎么在这种氛围下发展起来?
郑小悠:我觉得看这个矛盾我们要注意两点,一是国家思想控制的意愿和能力不是很一致,有时候意愿很强烈,但不一定能做得到;另外一方面是皇权的意志和官僚系统体系的意志有时候也不完全一致。
清代很多文字狱和思想控制,像康熙初年的四辅政时期出了很多大案,最上层比如说皇帝或者一些皇帝身边的人,可能就是他们这些人的主观意志,为了加强对汉地的控制造成的。还有一些中下层趋炎附势,想借机上位而提出的事情和上面的意志结合形成的合力造成的。
但以明清时期,包括清代官僚系统的执政惯性来说,其实也不太具有一以贯之对社会高压控制的能力,因为这需要很高的运作成本。比如说我们看黄六鸿写的官箴书,他说在基层政权的州县地方官主要有三个职能:刑名、钱粮、教化。钱粮就是税收。一个州县官收税达不到要求,比如说六七成以上,是要受处分的,甚至乌纱帽都保不住的。刑名的科条也非常严格,审一个冤假错案,这个官帽就要丢掉。比如说故入故出,故意判错案子,或者无意地判错案子,轻了或者重了,都有相应的处分的。所以官员在这方面要投入很大的精力,包括对他聘请的这些师爷,或者对书吏、差役都要投入大量的精力。
但教化这种东西相对来说比较软性,在国家的六部科条考核上没有很严格的考核标准。比如说朱元璋非常强硬地要求每家每户都要买《大诰》,学习《大诰》,《大诰》四编都要。如果家里有《大诰》,犯了罪可以减一等,如果没有《大诰》,犯罪会加一等。但实际上朱元璋一死,这一条就废弃不用了。像朱元璋这种是非常严苛的,而且《大诰》是有明文可以学习的文本放在那里的,其实也就持续几十年,就不了了之了;更何况清朝没有这么强势的文本学习的要求。所以其实统治者的意愿、最高追求和日常能达到的管理效果之间会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另外是官僚集团,特别是大多数个体很怕麻烦,越简单越好,把任务完成,考核没问题,这对一个普通官员来说是最重要的。至于说大清天下万年、满洲皇帝能做多久的皇帝,这些跟知县、知州的关系并不是特别直接,所以对这个的执行力他自己也是打折扣的。如果下面出了事最好把这个事儿压下去,而不是挑起来。除非碰到那些希望借此有所表现的官员,还是极少数个别的官员有这样的做法,大多数人还是压事儿不挑事儿的。
我觉得明清社会的文化或思想的大发展、大活跃主要还是跟社会的普遍需求密切相关,而不是自上而下政策性、强制性的要求。像天理教起义以后,天理教很多秘密会社都是崇拜小说人物,像崇拜刘关张、崇拜孙悟空。我们一般认为嘉庆年间的文字狱已经非常宽松了,从乾隆后期到嘉庆初年已经废弃得差不多了。但在嘉庆十八年之后又兴起了一轮禁小说,像《水浒传》这样反朝廷性质的小说被强行禁止了一波。这一波为了应对天理教起义,把这些民间会社崇拜人物的相关小说查禁了,但这个时间非常短暂。而且大多数秘密会社等底层的人员不是通过阅读来学习,而是通过听戏、听书,你把文本禁了没有用,照样在底层民众当中口耳相传,这无论如何也禁不了。这就是政策和统治者意愿和实际民间文化发展的落差,这个很明显。
王敬雅:谢谢郑老师,除了对历史的探讨和了解,我们也想聊一聊关于历史书写。先说说微观史学,其实微观史学写作存在着一种套路,也就是将这种小人物嵌套到历史当中,历史的宏观设定是我们既知和既定的。所以我们在嵌套的过程中特别容易发生同质化。我们四位老师在写作中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先请郑老师谈谈对微观史学写作的看法吧。
郑小悠:我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最近在尝试写一系列的基层官员。我之前也做过一些人物的研究,按我导师郭润涛老师的话说,年轻人不应该做人物研究,因为年轻人对人的把握不够,不一定对史料把握不够,但会对人的把握不够。
我很同意他的说法,写人物不管是大人物、小人物,主要靠两方面的能力。
一个是对史料把握的能力,这一点来说我们从事专业史学研究的人是比较有优势的,择取史料,然后囊括尽可能多的跟这个人、这个时代有关的文献,然后去辨析它,这是我们擅长的。
另一个就跟你专业的技能关系不是太大了,与人际关系的敏锐程度关系更大。我觉得如果写成学术论文或者写成学术专著,对史料把握、搜罗的能力更重要。但如果写一个非虚构作品或者做偏于大众性的历史写作,我想对人的把握更重要。
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不太存在王老师说的同质性的问题。因为每个人,他的人生,他的生平、事件、情感经历是完全独一无二的。有两个人可能结果一样、过程一样,但他的心路历程、他的想法、他的出发点肯定也不一样,所以千人千面,这是写人物最大的魅力所在。
我们研究制度史可能会有套路,大多数制度都是从相对简单,到科条细密,再到发挥余地很小,最后执行不下去了,然后要另立一套制度,这些可能有同质化的过程。但写人不会,每个人都是他自己。
另外我们说所谓的大人物和小人物,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地位高低的问题,特别是政治地位高低;另一个就是史料多寡的问题。比如说罗新老师会说他写的王钟儿是小人物,其实她一点也不小,她是北魏皇帝的保姆,她有墓志,是一品女官,是一个很高级别的人物,史料少是另外一回事。又比方说邱捷老师写的杜凤治,他的社会地位比王钟儿低不少,他只是一个知县。但他史料多,他自己写的日记十几大本儿,完全可以被邱捷老师写成一个历史作品的主人公。所以,以王钟儿和杜凤治论,说他们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不是个身份问题,而是史料多寡的问题。所以其实人物不分大小,最重要的是把握他主体性的部分并尽量找到跟主体有关的这些边缘的、旁支的史料,最后尽可能凑成他的一生。
王敬雅:谢谢郑老师为人物研究开拓了更多的视野。接下来,冯老师,我个人有一个问题,对于您的明清时期,特别是晚明士人的研究。我在读论文的时候,或者是写东西的时候我都特别会注意到关键词的问题,现在因为数据库的发达,我们经常会用关键词写论文,所有人物的,或者是关于士人的都是从某个关键词或者关键词扩展演化出来的。
但这个方法在冯老师的作品这儿失败了,我找不到关键词,也找不到您的数据库。我特别想知道,一方面您论述的这些人物不是像我们政治史有比较集中的史料,是各种文集、各种方志出来的,另一方面又没有关键词,您是怎么找处理的呢?
冯贤亮:其实我个人很向往像郑小悠老师这种微观史研究的方式,这种方式要求高,不仅仅是技巧的问题,还有史料的准备。她刚才讲清代的条件比较好,还有很多档案,甚至是各种奏折里面都会有详细的涉及,往前面到了明代就少了很多。做得比较小的微观的案例也小不到正儿八经的那种小人物,因为如果想要做到像妇人研究,如《王氏之死》那样的状态要看运气,史景迁是因为用了三种材料:方志、州县的公文,还有小说,其实也要看运气。而且这三种材料都不是他作为一个小人物自己的言说,完全不是,很多是地方精英写述出来的,有的甚至只有三言两语轮廓性的表达,很模糊,这就造成了我们对于小人物研究的局限。元朝更不用说了,就更难了。我们经常有这样的奢望,是不是有像西方学界利用教堂里存有的大量小人物的故事档案,我们就不大有。
到了清代,特别是晚清以后可能多一点,但总量还是微乎其微。所以只能把目光落在知识精英上面,王老师提及的个案当中有两个比较小的,一个是秀才,一个是衙门里面的公务员,没有更高的身份了,这是我目前做的最小的两个案例。这个材料完全是通过史料的爬梳获得的,一开始没有想到用数据库搜索一下,完全是读史料,读着读着就找到了。这当然跟我的学习经历有关系,我以前喜欢研究州县行政,搜到一本我家乡的书,编年体的简史,写一个衙门里面,从明代崇祯年间写到康熙二十几年的历史,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个微卷,我在那里抄了几天,把它抄完了。数据库当然不可能有这种野史,遗漏了大量精彩的资料,包括地方志。我经常告诫学生不要依赖数据库,很多资料是数据库没有的,甚至有时候你以为查的资料够完备了,但最后的结论拎出来是不成立的。有些学生非常偷懒,他们不愿意自己手动爬梳史料。
王老师讲的那些我基本都是手动爬梳出来的,手抄了以后我非常震惊,史料描摹出来的历史,有很多地方和我们正史的叙述是相背离的。比如讲到康熙年间,我们认为康熙已经进入了清代的所谓盛世时期,但它讲的每一年都有问题,衙门里面的政治斗争,如衙门和上一级衙门的斗争,衙门和老百姓的斗争,知县和知县的斗争,屡见不鲜。
最有趣的一个例子是,顺治十八年“奏销案”爆发以后,江南遭灾最严重。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这些人除非将来还有机会考科举,重新考一遍才有机会往上爬升,绝大部分人是绝望了,再也不愿碰科举了,跟政治绝缘。但是我在衙门胥吏的描述当中,看到了康熙年间三藩之乱的爆发,对整个清王朝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并不只是对三藩之乱爆发的那些省影响非常大,对没有涉及的地方影响也非常大,就是在地方上征集大量的钱粮,要往战争区域运送。这恰好给被奏销的人带来了机会。
我看到一个吴江知县的案例,胥吏写得清清楚楚,这个人就是被“奏销案”革掉的,但国家需要钱,他就花钱买,恢复功名,然后做知县。这个例子非常重要,是我们以前研究三藩之乱或者后三藩之乱时代清朝的政治史,特别是地方政治史里面不太令人注意的地方。
第二个例子是秀才,秀才在江南这种地方是微乎其微的功名,因为江南盘踞了大量高功名的人,或者说乡绅、官绅群体,影响非常大,秀才算什么?秀才都只是微末之人,更不要说老百姓。这个秀才留下了一个笔记,其题目有点文学性——《说梦》。这个人生活在崇祯到康熙年间,完全是在乡下生活的。清朝建立以后,地方上要有大规模的改革,比如说赋税徭役的改革,他积极投身进去,也赢得了一些声望,甚至负责在地方上推动改革,在县府的指导下出面完成了很多任务。这样一个小小的秀才却承担了这么多的工作,或者说承担那么大的责任,是很罕见的,他都写出来了。
我从头看到尾,发现没有一句指责清朝不好。因为明清交替,江南知识精英对前朝的忠诚度非常高,动不动会有讽刺、挖苦,甚至用天灾人祸,一会儿虫灾、一会儿海里出现怪物这种怪异、变异的妖乱事件来讽刺当朝政府的问题,或者表达不满的情绪,但他没有。也没有涉及清初的文字狱,也没有说到“哭庙案”“奏销案”,我觉得这是一种透明的遗忘,他可能是刻意的,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这还只是一个抄本,也没有刊刻流行。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把它写了出来。
另外一个是董其昌的曾孙,旁支的董含,他的功名被革掉了,他的笔记也是一个抄本,里面有大量的对康熙朝的不满,唯一表示满意的是三藩之乱后地方上形成了一种风气。什么风呢?一种讦告之风。比方说我和陈宝良老师是仇人,我诬告他,说他跟三藩之乱的那些叛逆之人暗中有勾结,其实没有证据,但只要这样一告,一告一个准。这股风气从地方一直刮到朝廷,康熙皇帝最后发了一个公文,说这个问题太大了,地方上有这样的风气是不好的,应该打压。董含对康熙皇帝的唯一称赞就是说下达了这样一个圣谕,“像我们这样的人可以高枕无忧了”。为什么他表示他可以高枕无忧呢?因为他出身比较高贵,是董其昌的家族出来的,曾深受这股歪风祸害。
像这类资料可以揭露出日常生活、王朝统治下社会当中非常微妙的政治脉动、地方士人对王朝统治的感觉和认知。这样的材料是没有进数据库的,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翻,有时候字还认不出来,因为拿到的本子清晰度不高,所以放大了很多也看不清楚,非常糟糕。
有时候要学学老一辈,我的老师辈是二三十年代的人,那一代的老先生值得钦佩,他们手动检索史料,整理出自己有兴趣的议题,然后写成一些给后来人带来很多启发的论文。这一套还是不可偏废,不能太过依赖数据库进行历史研究。
当然这些史料都进入数据库是很好的,但现在不可能都进入,这样的研究或者做学问的方式还是要继续保持。这样可能会发现意想不到的、有趣的史料,让我们做微观史和小人物研究的时候获得意想不到的精彩的效果。
陈宝良:时代的变迁自然会导致风气的变化。就历史的写作来说,现在有一种新的写作方式的崛起,即专门写小人物。这是很好的历史研究的转向,也是一种写作的转向。我们知道,“历史”这个词的本意,在希腊文中就是“讲故事”。在我们中国,同样具有擅长讲故事的传统。记得我刚上大学,进入历史系学习,每年寒暑假回到老家。那些乡老就会问我:你既然学了历史,那么讲的是什么故事?在乡老的记忆中,学历史就是要学会讲故事。在我们传统的史籍中,有很多历史书籍,都把故事讲得特别好,譬如司马迁的《史记》。但自从新史学崛起之后,如罗宾逊出版了《新史学》,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之后,我们的历史写作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即从叙述的历史转向分析的历史、解析的历史,更多的是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与研究历史,把讲故事的传统转而慢慢抛弃了。
说到明清社会的变迁,其最大的变迁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人的自我越来越高涨。在知识精英中,出现了很多讲究自我或人格独立的人。如明朝的苏州人阎秀卿,写了一本叫《吴郡二科志》的书。在这本书里,人物被分为文苑、狂简两类:一类是文苑中的人物,即纯粹的文人;另一类是狂简。文苑类所收人物,有唐伯虎、祝枝山等;狂简类所收人物,有桑悦、张灵等。收入狂简类的人物,就是那些为人放荡不羁之人。即使像唐伯虎、祝枝山一类的文苑人物,也都带有任情放诞的特点,如唐伯虎就称自己为“天下第一风流才子”。在明清时期,自我独立的知识精英越来越多,甚至可以说成群地出现。我前面提到的李卓吾,还有清朝的袁枚和毛奇龄,这三个人都喜欢收女弟子。我们知道,按照传统的惯例,读书人从事教学一类的工作,大都不收女性的弟子。李卓吾、袁枚、毛奇龄,作为儒家的精英,他们所独具的性格,以及收女性为弟子的故事,可否以微观的方式切入,重新加以叙事?我想这是很好的题目。这些人的生活越来越变得活泼,已经开始跳出了原先的刻板印象,即我们过去对儒家知识精英的刻板印象。这就为微观写作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与素材。
知识精英内在的心灵,如何加以印证?小人物的历史又该如何创作?我觉得,非虚构创作可以看作是历史写作的一种新潮流,也是特别好的一种写作形式。我一直是这么想的,心向往之,但力不从心。反思自己,觉得自己缺乏这种写作的能力。即使如此,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像郑小悠老师这样的非虚构创作的历史作品涌现出来。这应该说是我真实的想法。
王敬雅:谢谢陈老师给我们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接下来有请吴老师。
吴琦:这个学期,我给博士们开设了一门课程《新史学及其研究》,我让博士们研读学术成果,其中就有,比如刚才敬雅老师谈到的《奶酪与蛆虫》,比如《蒙塔尤》《叫魂》等,这些书对很多同学来讲,本科阶段就有可能看过,但到了博士阶段拿来研讨,研讨什么呢?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提升博士们的写作水平。《奶酪与蛆虫》是微观史的代表作,那就研读该著如何运用材料进行微观的研究;《叫魂》是事件史的代表,那就看怎么利用一个事件去揭示历史和社会深层的东西;《蒙塔尤》,我是希望博士们在研究的过程中更多地注重我们怎么从一个区域去揭示社会变迁。
我给博士们的书单列了多种书,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了学术研究之门,你必须要对各种研究方法、研究路径有了解,以后遇到各种材料之后,你才可以很好地去解读和把握它。
我觉得小人物可能不是大历史的主体,但一定是构成历史最为重要的血和肉,没有这些血和肉,无法建构完整的历史,这是毫无疑问的。
微观史是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一个重要的路径,我没有做微观史的研究,但是以后一定会去尝试,因为有一些材料我已经在积累的过程中。我这几年做的研究会涉及微观的东西。
我做漕运研究,即将在“大学问”品牌出版《漕运与中国社会》修订本,这本书是从制度史和经济史的角度展开的,当然就是宏观的把握。后来我的《清代漕粮征派与地方社会秩序》一书,把漕运落实到地方。再后来做的国家项目《清代漕运对区域社会环境影响的实证研究》,书稿也出来了,但一直在修改。
这几年还在做什么呢?运漕家族研究。该项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具体而微的资料的收集。家谱资料用数据库搜索是不行的,虽然有一些家谱进入了数据库,但还有很多家谱其实都是散存于民间的,必须要深入民间收集,依靠大量的田野工作。
这些年我们收集了不少家谱材料,看到很多运漕家族到底怎么年复一年地应对国家下达的运漕任务,包括家族在规制中的应对漕务的方案、家族宣扬运漕事务对家庭每一位成员的意义,以及运漕事务对家族发展的重大作用,等等。不少家谱记载了具体而微的内容,比方说家族里某一个人,在某一次运漕过程中遇到漕船漂没,人死了,家谱里面会因为他给“天家”做事而亡,予以大肆的表彰,这些生动、感人的例子会写得很详细,这对我们来讲就是宝贵的材料了。
我不是用来做微观史学的叙事,我是想论证制度在基层的实践。制度如何在基层实践?通过阅读这些运漕家族的家谱,我们发现千族各面,同样是一个制度,制度上的规定都是一样的,但不同的家族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就像上午讲的大家族和中小家族应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路径也不一样,引发的问题也不一样。所以我用很多微观的材料论证制度的实践。
小悠老师直接利用微观史料做深度的揭示,这比较真切地落实到了微观史学上。另外,你有了好的资料,用以论证比较宏阔的问题,这也是可以的。
我们讲的微观史料或者小人物的史料一定是比较散见的。刚才贤亮老师讲了,很难系统性地找到某一个小人物方方面面所需要的材料。如果你遇到了,对你来讲可能就有一个大运气了。材料的积累是日久的,逐渐地结合你的研究对象一步、一步地深入,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超预期的收获,也常有意外碰上好材料的情况。曾经,我们收集湖北的民间文献,做田野的时候收到一些女性的抄本,这对做性别史就是很好的材料。
我比较赞成前面几位老师说的,数据库也好,电子文献也好,大家可以用来做搜索、检索,但起步之时最应该看纸质的文献。第一是要全面地看,而不是简单地用关键词。我曾经和同学打比方说,写一篇论文,如果我用了50则材料来支撑,解决问题,那么我反过来做,我先给你50个材料,你能不能写出论文来?写不出来。因为在文献阅读的过程中还同时涉猎、认识很多支撑性的内容,帮助你理解研究对象。如果你仅仅是检索,关联知识的涉猎是缺失的,最后缺乏全面而深入的理解,最后只能是史料的堆集。
所以我的建议是以纸质版书籍的阅读为主,边读边理解,边思考,更容易产生观点。但研究是可以利用大数据的,用电子文献做检索。做学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道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径,各位老师讲的东西可以给各位同学参考,我们毕竟是过来人。但你们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你们的研究对象,具体问题具体处理。
王敬雅:谢谢吴老师,吴老师说到特别重要的一点,虽然我们今天把微观史学当成一个问题在讨论,但不是所有的写作都以微观视角来切入,毕竟我们的历史还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
最后还是想讨论历史写作本身的问题,就是经常说到的好的故事和好的历史。这两点在明清史学的研究中特别明显。大家其实最早对于明清史学的了解都来自电视剧。很多人对明清历史的了解就是一个一个的传奇故事,但当我们真正接触到历史学习之后,就会发现历史研究本身跟讲故事的结构是不同的。
本来这件事如果不把它写得故事性一点,按照历史研究的路径去写会有点无聊;如果写得故事化、冲突性更强,又会削减掉很多必要的材料和细节。各位老师书写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郑小悠:无数人问过我雍正继位的问题,以我的认知来看,我觉得历史比影视剧或者传奇故事更有意思。比如一直很火的《甄嬛传》,我就觉得这有意思吗?多无聊啊!从雍正的视角来看,天天跟他汇报哪两个妃子又掐起来了,谁又流产了,这对他来说有意思吗?我觉得很没意思,他肯定也觉得很没意思,因为他当皇帝的,他如果想有这样的经历是很容易实现的。但他的人生是从一个相对边缘的皇子的位置,一路处心积虑杀到权力中心,然后利用自己的种种手段走到现在的位置。他觉得这样的政治人生比三宫六院更有意思。
所以我写九王夺嫡的历史故事,虽然我最后无法判定雍正到底是怎么继位的,因为这不可能判定,康熙都不知道,他身边的那些皇子、兄弟都不知道,或者只有那个极少范围的人能明确知道他是怎么继位的,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你做多少研究、看多少材料也不可能,因为这是宫廷秘辛,不可能得到确切答案的。
但通过我掌握的史料,加上我个人对当时政治社会背景的认知,把它以我的视角描述出来,我觉得这个过程,比《甄嬛传》之类的要有意思得多。而且因为我们写东西、出版,目标读者是有一定群体性的,而不是广撒网,所以我在写作中不追求《甄嬛传》的那个效果,还是把我认为更有意思的材料尽我所能整理出来,然后希望让跟我有一样审美价值的读者认为有意思就可以了。
到现在为止,我做过专业的学术研究,写过论文、学术专著,写过历史非虚构的作品,还写过历史小说,针对这三者的差异,我做过一些比喻。
我认为写论文或者学术专著其实是一个用原木——用金丝楠木最好,铸造广厦的栋梁的工作。金丝楠木和各种重要的木材就是史料,我们就是在辨析、寻找出优质史料的基础上稍微做一点加工,让它拓展学术边界——说大一点,拓展人类对历史认知的边界,达到一点点这个目的就可以了。
而非虚构的写作是基于史实相对大众化的创作,我就比作做木雕。木质的选材要好,不能要朽木,但要求不像要造一个太和殿的木柱、大柱子这么高,可能多方的都要选择,因为要让更多的人接受。然后我在精加工的技巧上要求更高,木雕做出来是一个让大家都欣赏的工艺品,但能看出是优质的木材做的,这就达到了我的目的。
至于写历史小说就好比做木制玩具,这个对木头要求不高了,包括笔记小说,越是民间的、稀奇的、故事性强的、有吸引力的、别人没见过的越好。当然也要符合写作的时代,因为我是专业出身,对自己有要求,不能胡编乱造,不能把唐朝的事儿说成清朝的事儿,这个做不到。但对木头要求不高,可以配各种塑料的、皮质的、人造革等各种材质,拼接在一起,最后这个玩具可能都看不出是木制的,但它是一个好玩的玩具,能吸引小朋友去玩,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
所以写历史小说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可读性、故事性,但是也传递出一种比较强的历史感,能让大家读了之后有知识性的提高。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点写作经验,各位同学以后有愿意从事相关工作的可以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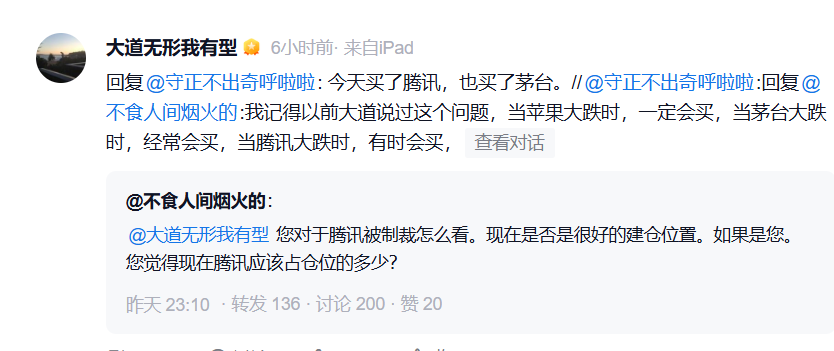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