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著,蓝江译,中信出版社,2025年1月版,128页,68.00元
添加微信好友, 获取更多信息
复制微信号
在2019年,中国思想界、读书界有过自发地庆贺哈贝马斯九十岁生日的研讨活动,德国学者斯蒂芬·穆勒-多姆(Stefan Müller-Doohm)的《于尔根·哈贝马斯传: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刘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在此时推出,我也马上写了该书的书评。我在文章中认为在今天谈论哈贝马斯,最值得珍视的是他在喧嚣的政治抗争的争议中保持独立思考的立场和道德勇气。当时主要指的是在1967年德国学生抗议运动中哈贝马斯一方面谴责警察枪杀学生的暴行,呼吁以公共抗议来抵制逐渐显形的“威权主义绩效社会”,但同时也反对过激的“左翼法西斯主义”挑衅行为,结果是陷入持续的激烈舆论风暴之中。他的助手耐格特认为哈贝马斯力图坚持的自由主义立场的解放功能久已被证明具有欺骗性,但是哈贝马斯仍然坚持要通过自由和公开讨论获得最后的决断,坚持决断必须依赖于论证的力量,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强迫,他一直坚守和强调的是公开讨论对于政治抗争的合法性的重要作用(参见《于尔根·哈贝马斯传: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的相关论述)。没有想到的是,年过九旬的哈贝马斯直到今天仍然活跃在思想论证的最前沿,我们还需要从他最新的著作中继续与他讨论如何通过公共讨论证成政治抗争的合法性问题。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的《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Ein neuer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d die deliberative Politik,2022;蓝江译,中信出版社,2025年1月)无论从主题、内容还是问题意识上都应该看作是他在1962年出版的成名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1962;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的续篇,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不妨把这本新书作为旧著的新版导言。这本书的缘起也的确是这样,哈贝马斯在“前言”中告诉读者,该书源自他的同事马丁·泽利格(Martin Seeliger)和塞巴斯蒂安·萨维尼亚尼(Sebastian Sevignani)发起的关于我们当前是否应该谈论公共领域的“新”结构性变化的探讨,很显然这是以他在六十年前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作为讨论的起点,这无疑激励了他重新审视这个老问题。当泽利格和萨维尼亚尼为《利维坦》(Leviathan)杂志特刊征集的稿件的时候,他为该刊写了一篇文章,本书就是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补充了有关协商政治概念的两个解释而写成。在他看来协商政治取决于政治公共领域的开明民主决策,为此他把该书提供给更多普通读者阅读(“前言”第1页)。
因此首先应该回顾一下。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通过梳理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共领域的历史形成过程,提出的核心观念是在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机构之间存在一种公共领域。欧洲社会的旧式公共领域被上层社会和贵族社会所垄断,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只有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才能出现。这种公共领域处在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之间,一个私人组合的、有阅读与讨论兴趣及能力的群体开始在咖啡馆、沙龙和宴会上出现,开始形成的是文学公共领域,很快就扩展到具有政治讨论和舆论影响功能的公共领域。关心公共利益,通过公开、自由和理性的讨论形成公众舆论,从而影响政治决策,这是公共领域的基本概念。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看,哈贝马斯的这种理想的公共领域依赖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公私领域之间界限分明,各自相对独立;二是形成理性的批判主体,这一方面有赖于私有财产保障了公共领域里批判者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得益于文学公共领域提供的心理与智性基础。由公共领域而产生公共舆论,使资产阶级代议制议会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有了基本的依托,使法治国家宪政架构具有了在公权与私权之间的民意基石。总之,通过公共领域的理性讨论可以达到政治共识,形成国家意志。但是,这种自由主义模式的公共领域无法持久,当垄断性结构主宰经济生产的时代降临之后,社会的“结构转型”很快到来。原先维持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的结构发生严重变形:国家(公共权力领域)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被模糊乃至相互重叠,国家的社会化与社会的国家化趋势产生新的政治化领域,由自律私人组成的公众展开公开批判的政治公共领域转型为代表不同利益的公众组织进行政治妥协的场所,成为一种中介化了的政治公共领域。于是哈贝马斯在该书的第三部分试图通过对公众舆论概念进行社会学上的重新解释,为重新建立公共领域的独立性、批判性寻找对策,推动社会福利国家的民主宪政进程。
更值得回忆的是哈贝马斯的这本旧著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接受体验。或许不同的读者群体所关注的重点有不同,就我的阅读记忆——更准确来说是实践体验来说,当年“公共领域”这个概念远比“结构转型”的问题更能打动人心。对“公共领域”的词源学和历史叙事的了解很快就引领我们牢牢树立了“公共领域”是与“政治”“公民”等政治学概念同等重要的意识,最为关键和鼓舞人心的要义就是公民可以在公共的政治空间对所有公共事务、政治议题进行公开的、自由的讨论,通过理性的辩论寻求共识,从而对公共政策产生有效的影响力。从更为微观和感性的视角来说,在哈贝马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形成的历史叙事中有一些概念和历史描述与我们在九十年代末的想象、欲望等个体经验紧密相连。比如说到十八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住宅中的家庭成员越来越多拥有独有房间,与此同时是沙龙(客厅)的功能也越来越突出,文学阅读空间如何发展为公共政治议政空间,这些都能产生非常亲切的认同感。哈贝马斯在这本最新出版的《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中提到“该书不寻常的效果史”,认为“该书包含了对‘公共领域’的社会历史和概念历史的描述,这引起了许多批评,但也为更广泛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第5页)。他可能没想到仅仅是“公共领域”这个概念在三十多年之后给我们带来的思想冲击与实践勇气,从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前十几年的公共舆论中一直是一个核心概念,来自社会不同领域的阅读群体在书店、艺术空间、读书会等平台开展的智性活动也都怀有建构公共领域、促进公共舆论交流的思想意识。
应该强调的是,在这些思想研讨中的“公共领域”并非仅仅是一个来自西方思想家的概念化符号,而是在思想脉络和学理上形成以哈贝马斯的思想观念为中心的多种议题,真实地推动着知识界、思想界的理论探索。比如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使我们不断认识发掘“更佳论证的力量”的重要意义,只有这样才能使最后作出的决断建立在所有人自由、平等和公开地讨论的基础之上,才能产生真理与公正。从职业身份来看,哈贝马斯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关于大学改革的思想也是很有影响的,他坚决反对大学体制中的机构官僚化趋势,呼吁坚持大学的独立精神和科学的自我反省精神。尤其重要的是哈贝马斯在教育问题上的批判性反思正是他作为知识分子介入公共生活的思想历程的一部分,他对于自己身处其中的教育制度的关切也同时反映出他作为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始终在思考的主题:理论和实践、公共领域和民主、诠释学与经验主义之间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些思考中凝练出一个问题:一种坚持区分实然和应然的社会科学的认识和批判的自我反思具有何种地位?这个应然从何而来?怎样令人信服地进行论证? 英国社会学家杰勒德·德兰迪(Gersrd Delanty)在他的《知识社会中的大学》(黄建如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二十一世纪的大学应如何在与社会的交往中承担和巩固自己的公民身份,在书中也有专节论述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德兰迪认为大学就是一个植根于交往、批判性和改革性的场所(83页),与现在我们关注的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大学不应自外于公共领域,应该在新媒体时代积极回应公共舆论中事关政治决策等重大事项的争议。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是关于对民主体制的学习过程的认识,哈贝马斯在《“政治性”——政治神学可疑遗产的理性意义》(收入曹卫东主编《审美政治化:德国表现主义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中通过与约翰·罗尔斯的辩论而分析了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政治性概念与“理性的公用”的关系,他强调推进民主体制的进程是一个学习过程,指出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应该进一步穷尽宪法原则的规范性实质;而在全球层面坚持人权的普遍性意义,并且有必要为多元化的世界社会构想一个立宪框架(281页)。当然,哈贝马斯说的那种为历史研究带来的新的动力在我们这里也产生了积极反响,比如在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史学研究中,类似近代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公共空间”“公共交往”和“公共舆论”这样的关键词不断出现。由此更让人思考的是近代转型中出现的公共领域在二十世纪的历史风暴中遭遇了怎样的挫折,历史研究与时代转型的探索仍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可以说在一代人的时代记忆中,哈贝马斯带来了关于“公共领域”的历史想象与实践欲望,成为“新时期”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摇篮。
现在可以回到《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很值得关注的当然是“新结构转型”的提法。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领域的第二次结构转型。第一次如前所述,因为社会经济生产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无法保持独立的私人性,在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公与私之间的明确界限不再存在,出现了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双重趋势。因而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下的公共领域发生严重变形,公共政治舆论的包容性、独立性和批判性难以为继,公共政治中的“公众”转化为被大众传媒形塑的“大众”。这一次是在原来这种转型之后的结构中出现新的结构转型,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在高新技术加持下的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和无孔不入的泛滥再次导致公共领域走进前所未遇的困境。这一次哈贝马斯主要是从对全球现实政治急剧动荡的观察和思考中提出问题:在近几年来世界各国所经历的一系列宪政危机事件、区域战争、全球疫情中,一个明显的危机现象是西方世界在宪政制度下的政治党争极度撕裂,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竞争,究竟对政治危机产生什么影响?在社会舆情的社交媒体化和自媒体化的当下,公共领域的功能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应该说,哈贝马斯在九十多岁的高龄对现实政治剧变仍然有高度的敏感和深刻的思考能力,实在令人惊讶和敬佩。
哈贝马斯对于“新结构转型”的认识和描述是相当精准的:新媒体从公共领域的媒体结构来说,这种平台摒弃了传统媒体所扮演的新闻中介和节目设计的生产性角色,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迄今为止在公共领域普遍存在的传播模式。它们在原则上赋予所有潜在用户成为独立和平等的作者的权力。新媒体不生产、不编辑、不选择,通过在全球网络中作为“不负责任的”中介创造新的联系,并随着呈定额倍增的偶然和意外,启动和加强不可预测的商谈内容,它们深刻地改变了公共传播的特征。但由于没有专业的过滤,在内容上也没有受到监管,参与者之间关系的平等性和无管制性,“今天,这个伟大的解放承诺,至少部分地被分散隔离的信息茧房里荒凉的喧嚣所淹没”(32页)。应该看到的是,哈贝马斯对于媒体生产、传播模式以及消费群体的结构性变化的思考是建立在实证性资料和经验数据之上,他说的情况大致上我们都比较熟悉,比如传统的报刊媒体的衰落、社交媒体的急剧膨胀等,但是说到电视和广播仍然保持着最大的影响力,在我的感觉上这似乎与我们的经验似乎并不相同。哈贝马斯谈到欧盟国家在2019年底进行的一次调查统计,证实了目前各种媒体的服务和使用规模:“81%的受访者每天使用电视,67%的受访者普遍使用互联网,47%使用社交媒体,46%使用广播,26%使用报纸。”(35页)尤其有意思的是,电视和广播在“关于国家事务的政治信息”的需求中也保持着主导作用:在被调查者中有77%的人认为电视、40%的人认为广播和36%的人认为印刷媒体是他们的“主要信息来源”。这样的调查结果也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是否太快把传统媒体抛开了,尤其是这两天在关注地震的新闻时,发现在传统媒体(电视)与社交媒体之间的信息量存在悬殊差别。这提醒我们要关注一个问题:由于传统媒体的生产结构造成了接受心理的撕裂化,使舆情主流媒介的两极化日趋严重,结果是任何一方都难免陷入信息盲区之中。
尽管欧洲的调查表明传统媒体仍然保持巨大的影响力,引人注目的趋势是“假新闻对政治公众的日益渗透,特别是向‘后真相民主’的惊人发展,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在美国已成为一种可怕的常态,也增加了欧洲对媒体的不信任”(36页)。哈贝马斯深刻地指出:“人们对公共媒体的质量越来越怀疑,这可能与越来越普遍的信念有关,即政治阶层要么不可靠,要么腐败,或至少是可疑的。这一总体情况表明,媒体在供应方面的多样性,需求方相应的舆论、论点和生活观点的多元化,一方面满足了长期形成批判性和无偏见舆论的重要先决条件,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不同声音的日益不和谐,以及争议话题和意见内容的复杂性,越来越多的少数群体媒体消费者利用数字平台退回到志同道合者的信息茧房中。”这样的信息茧房正是我们所身处其中的真实境况,同温层的交流使我们在发现志同道合者的同时,忘却了还存在另外一个信息世界。
同样关键的问题是,“在我们评估媒体提供的服务导致接收者改变态度这一主观方面之前,我们必须看看使编辑性公共领域(redaktionellen Öffentlichkeit)日益歪曲的主观认识的经济动力。因为社交媒体所促进的这些接收模式的独特性不应该掩盖媒体结构转型的经济基础,而这种在前文已粗略描述的媒体结构转型,目前在政治上基本不受监管”(38页)。哈贝马斯继续指出,像脸书(Facebook)、优兔(YouTube)、照片墙(Instagram)或推特(Twitter)等这样的算法驱动的平台的表现从来不是中立的:“这些真正存在的新媒体服从于资本获利指令的公司,并且以其股票市场价值来衡量,它们也是全世界‘最有价值’的公司。它们的利润来源于数据的利用,它们为广告目的或以其他方式作为商品出售这些数据。……这些信息随意地‘粘贴’在其他服务上,反过来又使个性化的广告策略成为可能。这样一来,在算法的控制下,社交媒体也促进了生活世界背景中各类关系的商品化的进一步发展。”(38-39页)与商品化并行的是新媒体对政治公共领域产生的影响,“随着注意力经济的拓展,街头小报和大众传媒中早已熟悉的政治公共领域中的娱乐化、情感化和个性化倾向,在新媒体中也日益泛滥”(41页)。最重要的问题是“只有当我们把注意力从扩大的媒体结构及其变化的经济基础的客观方面,转向接收者及其变化的接收模式时,我们才会触及社交媒体是否正在改变其用户对政治公共领域的看法这一核心问题。当然,商业平台的技术优势,甚至像推特这样让用户制作简洁信息的媒介平台,为用户提供政治、专业和私人用途有着毋庸置疑的优势。这些进步并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问题是,这些平台是否也鼓励一种关于隐含或明确的政治观点的交流,这也可能通过改变使用模式,从而影响人们对政治公共领域的感知”(41-42页)。总之。新媒体如何影响和改变人们对政治公共领域的认识,如何对新媒体消费者对自身作为公民的自我理解产生影响,这是关键性的问题。
无论如何,“自由权利不会从天而降。首先,平等参与民主意志形成过程的公民必须理解自己是权利的创作者,他们作为自由和平等公民联合体的成员,相互赋予这些权利。鉴于这种重建,人们认识到民主的侵蚀,自从政治或多或少地让位于市场以来,民主侵蚀一直在扩大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民主理论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脉相承的。我并没有发明‘后民主’(Postdemokratie)这个词,但对于全球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后果的政治影响来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术语”(66页)。
那么,出路何在?如何面对“新结构转型”而重建独立、自由和批判性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提到了“守门人模式”,他认为“这种模式绝不意味着剥夺媒体用户的权利;它只是描述了一种传播形式,可以使公民获得必要的知识和信息,使每个人都能对需要政治调节的问题形成自己的判断”(33页)。不管叫“守门人”还是“审查员”,都是涉及媒体生产与信息交流的敏感问题,哈贝马斯也当然知道类似监控、过滤这样的概念会让人产生威权政治的联想,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如果政治公共领域要发挥其作用,产生符合协商政治标准的竞争性公共舆论,那么媒体系统至关重要。……只有当舆论制造者及其职能子系统的利益代表和公关机构,最后还有来自公民社会的各种行动者,对发现需要监管的问题有足够的反应,然后提供正确的输入,公共舆论才有意义。……技术上和组织上高度复杂的媒体系统需要一个专业化的工作人员,在公民凝结公共舆论的传播流中扮演守门人的角色(如现在所说的角色一样)”(26-27页)。这个问题当然会引起争议,我认为重要的是要把问题放在不同语境中分析和评判,不能“无问西东”地一概而论。应该说,主张让新媒体不受任何法律监护制度的约束、完全自由放任的观念是很少数的,问题在于谁来监护、依据什么以及如何监护。
哈贝马斯能够提出的解决方向无疑是诉诸完善的法律约束,就像他对社会科学的应然性思考最终是以法学伦理意义上的判断作为依归——他总是把“法律依据”作为解决公共问题的根本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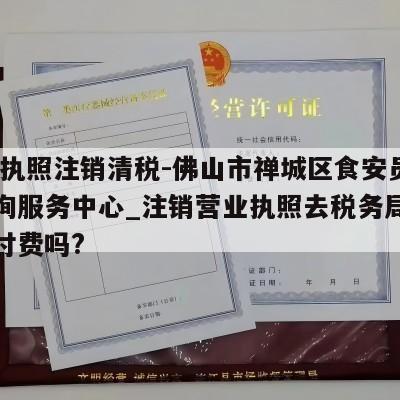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