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独特的世代。一方面,它与许多人心中典范化了的八十年代形成鲜明反差和对照,发生了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转折;另一方面,历史进程的顿挫所带来的知识生产方式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疏离和沉潜,又赋予它另一种内涵的丰富性,从而构成了此前和此后世代之间的独特纽结。在某种程度上,刚刚去世的出版人许医农先生正是这个转折时代的代表,而从这个转折时代过来的知识人应该是没有人不知道许医农这个名字的。
添加微信好友, 获取更多信息
复制微信号
我与许先生认识,完全是偶然。
1996年,我完成博士学业来到玉泉浙江大学任教,教学内容是与以往所学没有什么相干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当代政治理论。以此为契机,我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很快都转到当代政治哲学上。基于为台湾一家出版社撰写的几个小册子,在1999年前后,我完成了《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的初稿。我至今记得捧着刚出炉的书稿,在玉泉校区土木工程楼那个有些逆光的教室里,面对98级的研究生宣讲“当代政治理论”(这是我的课程名称)的情形。那时春寒料峭,同时蕴含着勃勃生机。
此前,我所在的单位在上海学林出版社筹划了一套丛书,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在那个系列中出版的。具体负责这套丛书的是倪为国编辑。也是因为这个机缘,我认识了倪编辑,并在随后把《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的书稿交给他,原计划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在那个年代,上海三联是一家颇为活跃和有影响的出版社。也许正因为如此,我的书稿在出版社躺了有两年没有什么动静。也是无巧不巧,同是上海三联编辑的汪宇先生有一次来杭州组稿,聊天间我提到有一部书稿在出版社待出。汪宇先生以一位出版人的敏锐指出,这类书稿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时效性”,最好不要拖得太久。还说他可以帮我把书稿推荐给其时主持三联哈佛燕京丛书的许医农先生。北京三联当然是一个比上海三联更大的品牌,更何况是著名的哈燕丛书,对此我当然是有些动心的。但是毕竟我和上海三联有约在先,所以我建议分两步走,一是我同意汪宇把我的书稿转给许医农先生,请她审核评鉴;同时,我也询问上海三联那边可能的进展。
现实的情况是,我并没有得到上海三联那边的及时回复,许医农先生却很快给出了反馈:她很欣赏和重视我的书稿,并打算以最快的速度让书稿进入评审流程。从汪宇先生那里得到这个消息时,我是既有些意料之外的,又有些意料之中的。意料之外在于,毕竟我自己对于那部书稿其实是颇有些不满意之处的,这当然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做出的自省;“意料之中”在于,许医农先生是一个出版人,我猜想,她一定是基于自己深厚的职业素养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准确判断出在当时的公共舆论和学术争鸣交集地带,还缺少这样一部论“学术性”也许有些贫瘠不足但其“指向性”却“丰富难能”的理论读物。现在回想起来,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辩证呢?!
此后不久,有一天汪宇告诉我,许先生其时正在南京开会,他建议我到南京与许先生进行一次面谈,一方面进一步听取她对于书稿的意见,另一方面也尽快把相关事宜敲定下来。
这就是我与许医农先生唯一的一次见面,我在南京她下榻的宾馆见到了她。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当晚的有些情形还历历在目。许先生开诚布公地说,我可以向她推荐在自己这个领域中最有代表性的评审人,她来组织评审。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我提到自己素所尊重的一位学者的名字时,许先生却断然予以否定。我惊问其故,许先生的回答是:这位学者的前妻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当时一面想许先生毕竟是个老革命,一面却也“心悦诚服”了下去而一声不吭了。
书稿评审过程一个最大的收获,是我藉此得以和李强教授建立了联系,并听取了他的意见——他尤其中肯地认为我对于自由主义的研究有待深入。在某种程度上,书稿正式出版时作为附录的“政治理论史研究的三种范式”也是在听取李强教授的意见后增补上去。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为书稿中自由主义部分的分量之菲薄感到汗颜,另一方面却也为这篇附录曾经得到李强教授的赞扬和肯定而感到欣慰。
收到《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这部书稿时,许先生已经进入职业生涯的末期,在把评审人的意见转给我并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后,她就从三联的岗位上退休了。这部书稿后来是由孙晓林编辑接手的,部分因为这个原因,我在此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许先生,一直到昨天午夜得到她逝去的消息。
无论如何,在许医农先生这位“伯乐”的关注下,《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终于由三联哈佛燕京丛书出版了。这固然要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回想起来——无论当其时也,还是多年以后回顾,除了那年在首师大听陈来教授说出那句“《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还是写得不错的”,我自问从来没有什么特别兴奋之情,而充其量只有绵延至今的“执拗的低音”。甚至说得夸张些,对于一个其实并不算是完美主义者的我来说,《从自由主义主义到后自由主义》很多年来竟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要到《当代政治哲学十论》出版后才基本放了下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孙向晨在他的书评中犀利地指出后者乃前者之“余绪”,可谓知我之言。
《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无疑只是一份过渡时代的微薄产品,它既不足够“思想”,也不足够“学术”;既不足够“理想主义”,也不足够“经验主义”。说到这里,我就想起,由其胞弟陈敏之编纂的顾准最早的文集即名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初版是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1990年初,我在淮海中路622弄7号求学时,图书馆还只能借到顾准的遗著《希腊城邦制度》,而其时刚出版不久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在社科院门口那家至今尚存的沪港三联书店见到的。等到由许医农先生责编的《顾准文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我已经转到杭州求学,当我在湖畔居的杭州三联书店买到这本书时,自然想不到不久后自己会与许先生有这样一段生命中值得珍视的交集。
哈佛燕京丛书尔外,许医农先生在三联最重要的工作应该就是那套著名的“宪政译丛”,当年我曾在杭州的大街小巷追买这套书。除了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这套丛书让人最为印象深刻的是两本小册子,分别是爱德华·考文的《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和卡尔·弗里德里希的《超验正义》。2007年,我在普林斯顿访学,之所以会留意到普大校园里的考文楼,就是因为前面这部小册子。而我是不久前才从朱迪斯·史克拉的一次演讲中得知,原来她在哈佛的导师就是弗里德里希。
在题为《学问人生》的演讲中,史克拉追溯了她作为一名出生于里加的犹太难民在美国政治学界的成长史。她剖析了麦卡锡主义隐秘微妙的影响:“年轻学子以不当知识分子为荣。在许多学生当中,除了运动和自命不凡的说长道短,就容不下别的话题!成日吹嘘的是令人反胃的隐私,换衣间的玩笑话和以卖弄为特点的伪阳刚气”。
作为哈佛政府系第一位女性正教授,史克拉坦承自己从未想过把职场上遭遇的困难转化为意识形态的问题,而这并不是她并未自称真正的女权主义者的唯一理由,因为归根到底,“参加一场运动,服从一种集体信仰的思路,在我看来是对知识分子价值观的背叛。这个信念在我作为一名政治思想家所谋划的将哲学与意识形态分开的工作中,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具有自由主义特点的事业——一个悖论”。
《民主新论》的作者萨托利在引用了布赖斯的“卢梭已燃起上千人的热情,边沁主义才说服了一个人”这个警句后曾经感叹:“理想主义周游四方,经验主义足不出户”。他还说,“理想主义方法和经验主义方法倘能殊途同归,对双方都是幸莫大焉”。顾准大概既没有读过萨托利,没有读过史克拉——准确地说,均出生于二十年代的这两位作者应该都是顾准的异代知音。
“萧条异代不同时”,而在我看来,与史克拉同样地出生于二十年代末的、同样地辩证于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许医农先生肯定是会赞同这三位作者,并欣然与他们为伍的。
(2024年10月13日午后于吴泾大荒)
-----
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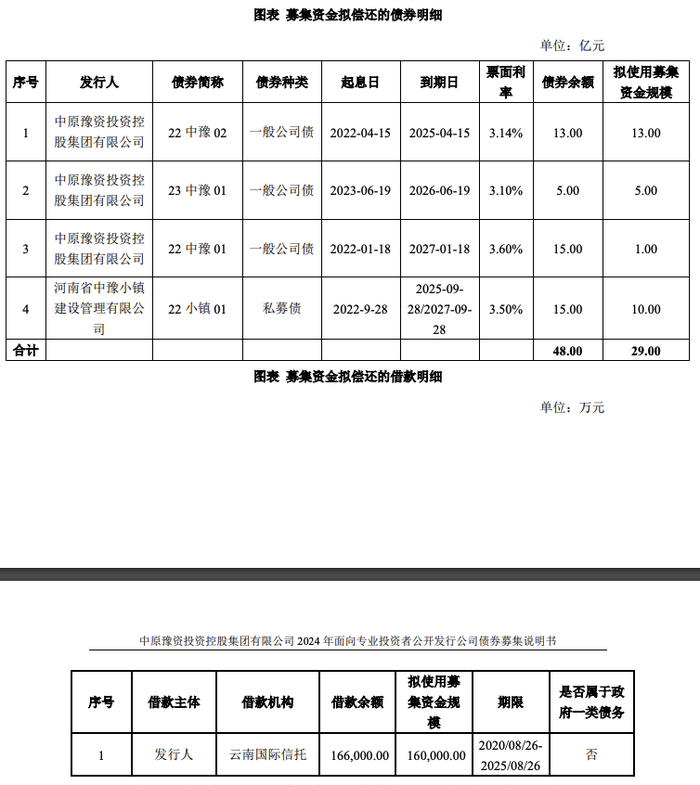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