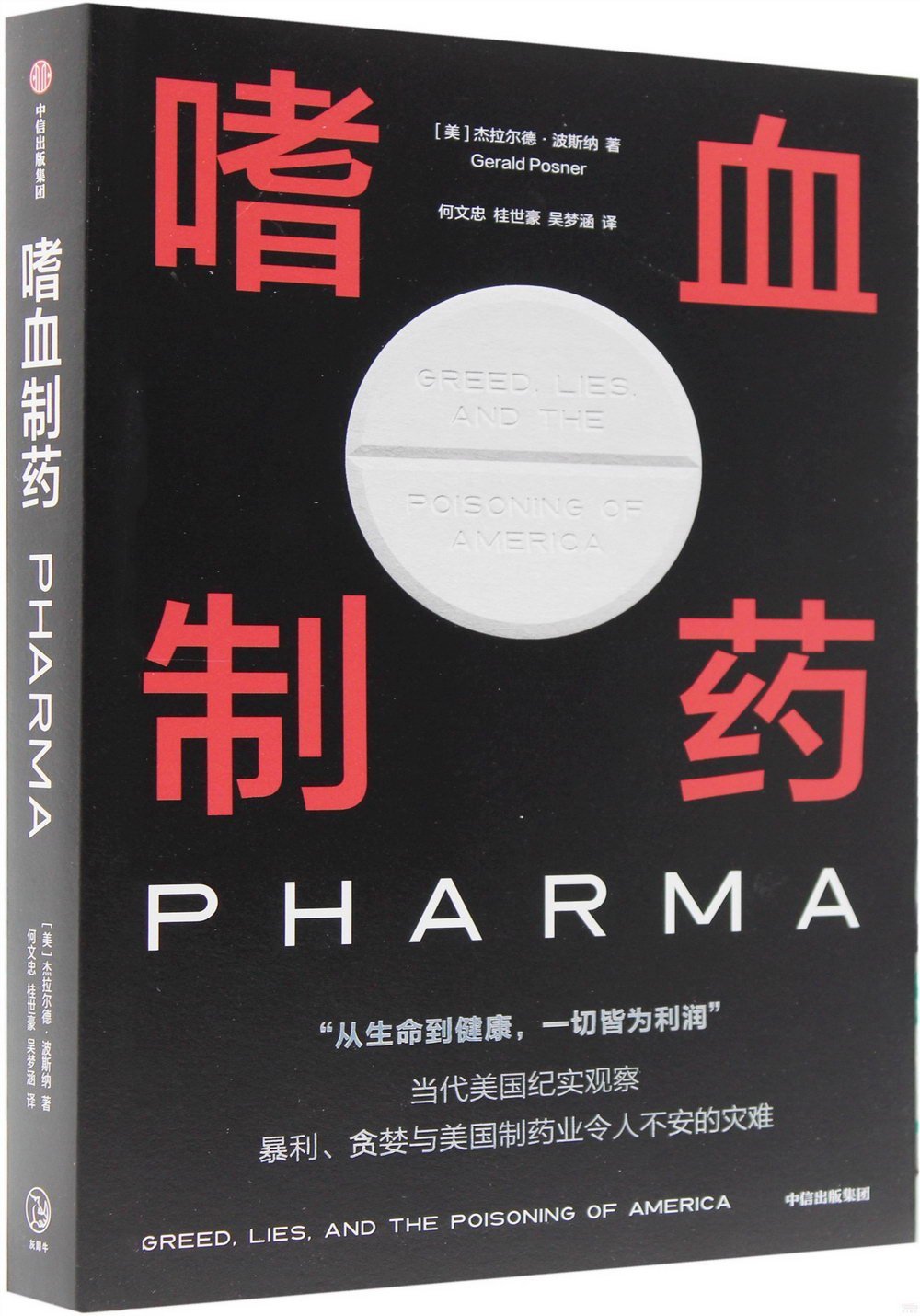
《嗜血制药》,[美]杰拉尔德·波斯纳著,何文忠、桂世豪、吴梦涵译,中信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516页,88.00元
添加微信好友, 获取更多信息
复制微信号
2021年10月,一部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视剧《成瘾剂量》(Dopesick)在美国引发热议。该片讲述了普渡制药(Purdue Pharma)研发的阿片类药物奥施康定(OxyContin)的流行史,揭示了商业媒体、药品销售与学术会议共谋下的公共卫生危机。几乎同期,社会学期刊《美国社会学评论》刊发论文探讨阿片类药物如何重构疼痛管理范式(Jane Pryma, Technologies of Expertise: Opioids and Pain Management’s Credibility Cri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22, 87[1], pp. 17–49)。这两起事件标志着药物过量问题从专业领域进入公共话语中心。

电视剧《成瘾剂量》海报
在故事之外的,美国社会的药物过量危机已经长达数十年之久。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数据,2022年全美药物过量致死人数达十万七千九百四十一人,其中阿片类药物致死占百分之七十六。尽管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宣布为应对阿片危机,美国进入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然而这一局势并没有得到迅速缓解,2023年美国阿片类药物相关急诊访问总量仍然居高不下,约为八十八万一千五百五十六例。面对这一持续恶化的形势,我们不禁要问:实验室中产生的小小药片如何造就了全社会的危机?
美国著名调查记者和作家杰拉尔德·波斯纳(Gerald Posner)的《嗜血制药》(Pharma: Greed, Lies, and the Poisoning of America)为此提供了历史病理学视角。该书以十九世纪专利药泛滥为起点,以普渡制药背后的萨克勒家族刑事认罪为终点,展现药品研发、监管博弈与资本扩张的共生关系。作为一本非学术纪实作品,作者没有严格按照时间序列安排章节结构,而是通过截取不同时代的碎片,呈现时局中人物之间的考量与周旋。全书共有五十二章,章节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作者由此编织出富有张力的历史图景。
基于本书提供的历史细节和相关文献,我将美国制药业百年史分为四个阶段。在每个时期内,大部分美国制药公司都会围绕一类药物(专利药、抗生素、重组基因和精神类药物)开展研究并与监管部门进行博弈,而这些从实验室“诞生”的药片给当时的社会甚至全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在结论部分,我将在制药业放置医疗化(medicalization)脉络下,讨论该书在论述中的一些欠缺。
专利药时代:监管真空下的狂欢
美国制药行业兴起于殖民地时期,并在内战时期实现第一次繁荣发展。在十九世纪中叶,为了“满足作战部队对抗菌剂和镇痛药空前大的需求”(第8页),吗啡、可卡因、鸦片酊与乙醚与乙醇的混合物凭借其令人镇静或兴奋的功效占据了药片市场。众多制药公司借此契机推出了各种药品,例如“默克公司吹嘘粉状吗啡的纯度,其最受欢迎的产品之一是含有鸦片成分的止咳糖。施贵宝和辉瑞销售了十几种不同的鸦片酊”(1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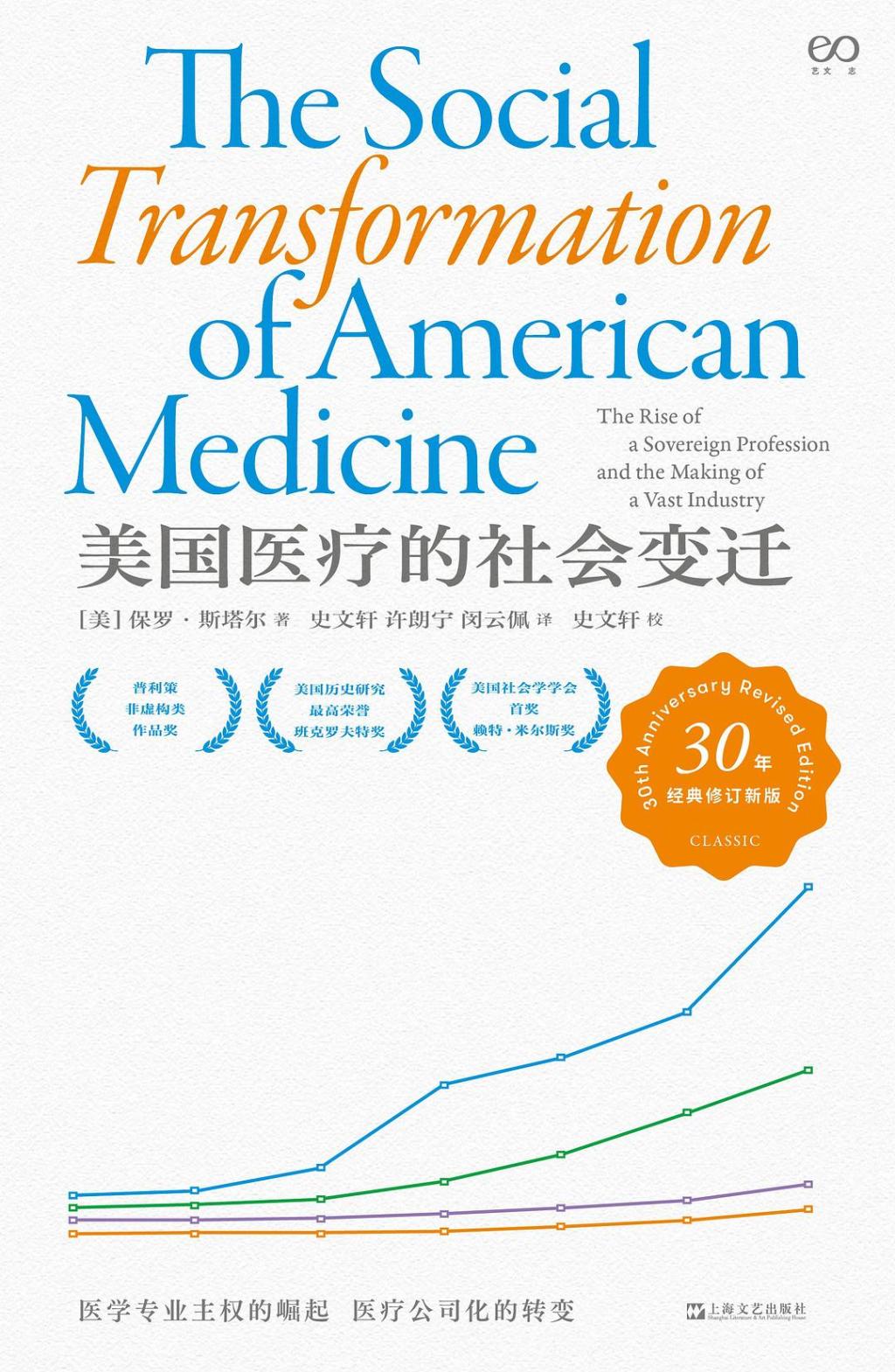
由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政府并没有颁布全国通用的医疗执照(Paul Starr,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Basic Books, 1984),美国医学会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Owen Whooley, Knowledge in the Time of Cholera: The Struggle over American Medicin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任何人只要懂得用药,便可称自己为“医生”。制药行业的加入更是加重了医疗领域的混乱程度。默克、施贵宝、辉瑞等制药公司开始鼓吹自己生产的“神药”具有其他药品难以媲美的功效,并且将其药品视作自己独有的专利。在二十世纪初,美国政府虽然开始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但并没有规定药品必须证实自身的功效。由此,制药公司“利用知识产权法来保护药物名称、药瓶形状甚至标签设计,同时,他们都对处方秘而不宣”(11页)。这种“技术黑箱”使患者维权陷入困境——制药公司总能将副作用归咎于个体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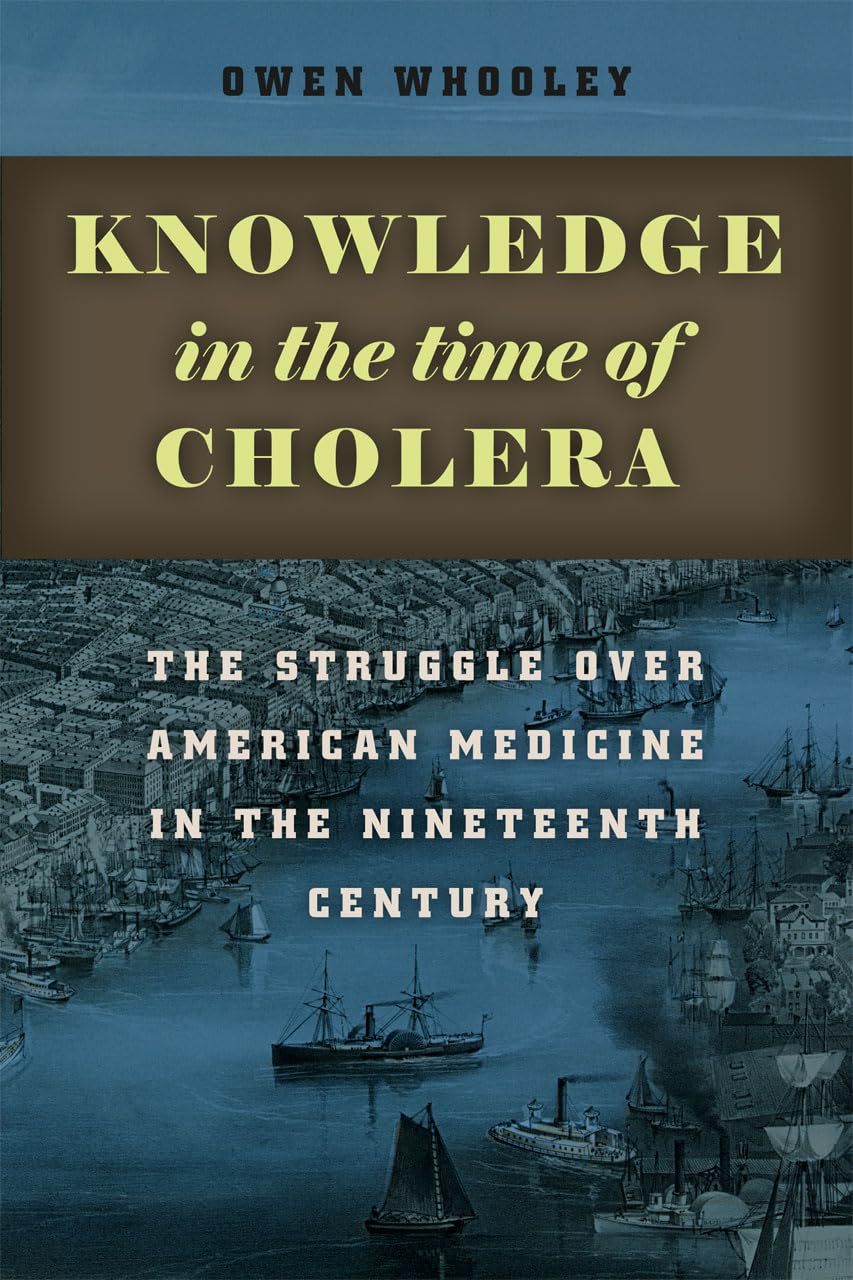
“专利药时代”给当时的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负面影响,由此吸引了美国政府的注意。在1906年,美国政府颁布《纯净食品和药品法》(Pure Food and Drugs Act),规定药品标签必须准确反映其成分(James Harvey Young, The Toadstool Millionaires: A Social History of Patent Medicines in America before Federal Regul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以此限制日渐猖獗的制药行业。然而,这一举措未能遏制行业乱象。据作者所言,一种鼓吹能保持健康的神药“在标签上列出了可卡因,但没有修改这种未经证实的药品的疗效”(23页)。换言之,这些公司尝试让公众得出如下结论:有成分标签意味着药品不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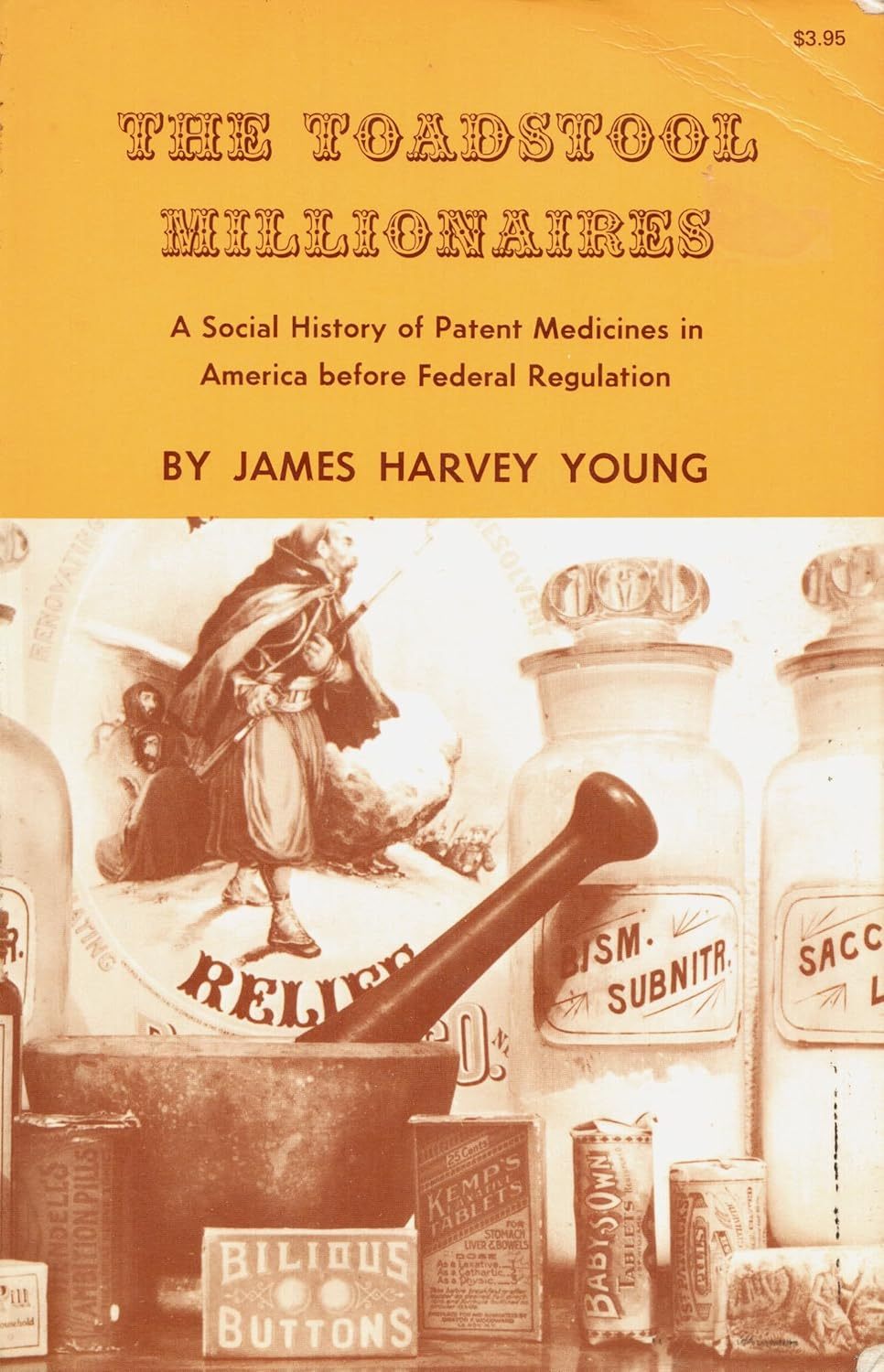
直到1914年《哈里森麻醉药品税法》(Harrison Narcotics Tax Act)和1919年《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Eighteen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明确管控专利药的核心成分——麻醉药品和酒精后,专利药的时代才正式落幕。
抗生素时代:道德与盈利的平衡
在作者以讽刺口吻介绍专利药的血腥历史之后,围绕抗生素的描绘则略显温和。青霉素在美国的兴起充满了偶然因素。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最先发现了这一要素,但当时“英国已经与纳粹德国交战近两年了”(33页),政府无法提供更多资金来支持其研究。科研人员便赴美寻求制药公司的资金支持。然而,出于盈利的考虑,“没有一家制药公司愿意将主要资源投入一种实验性药物上”(37页)。令人意外的是,此时的美国政府一反常态,宣布青霉素生产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并且鼓励制药公司开展研究,宣称其研发不受反垄断法的约束。
在“国家安全”的话语下,制药公司不仅将其自身塑造为关注民生的“道德企业家”,更是围绕抗生素展开了前所未有的竞争,由此大幅缩短了抗生素的发现与生产周期。我们只需列举不同抗生素的诞生时间便可了解这一段药物研发史奇迹:青霉素(1928)、链霉素(1943)、金霉素(1945)、红霉素(1949)、土霉素(1950)、四环素(1953)、万古霉素(1953)……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并没有止步于抗生素研发和普及的线性历史叙事,即“正是因为抗生素的发明,造成了未来数十年间滥用现象频繁和细菌耐药性的不断增强”,反而关注到制药业作为抗生素滥用的重要幕后推动力,挖掘了制药公司为推广其药品构建出的新型知识-商业网络:面向医生的直销。在此之前,制药公司主要依赖第三方广告公司和私下交流推广药品,而普渡制药的创始人亚瑟·萨克勒认为,“不能再像在教堂推销产品那样,与坐在旁边的人低声耳语。亚瑟认为,是时候发展能够亲自拜访数千名医生的销售部门了”(77页)。因此,制药公司逐渐将目光投向了权力日渐上升的医生群体,开始通过直接联系、发送广告邮件、赞助学术会议、在学术杂志上打广告、提供免费样品等方式干预医疗决策。医生也并非铁板一块,不少人热衷于获得意外收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医学会杂志》一千五百万美元的广告收入占美国医学会收入的百分之四十”(88页)。
在此背景下,抗生素滥用现象开始出现。由于抗生素当时被视为“神奇子弹”(magic bullet),其广泛使用缺乏适当的监管,耐药菌株得以迅速传播。伴随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在医院环境中的爆发,抗生素滥用的后果逐渐显现。书中开头论述的“超级细菌”一例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当制药公司逐步垄断了各自在抗生素领域的生态位时,分子生物学推动下的重组基因研究进入制药业的视域之中,后者围绕基因的研发开启了制药业的新时代——重组基因时代。
重组基因时代:从发现到发明
在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获得学界广泛关注之前,制药业生产药物的逻辑更多是“发现”,即研究者从自然界偶然发现了某种物质后,放到实验室加以隔离与发酵,进而生产出可以大规模复制的药品。书中围绕不同抗生素的发现过程进行了极为详细且有趣的介绍,在此不做论述。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领域,分子生物学将生物学的研究对象转向分子层面,挖掘遗传信息如何得以存储,基因与基因组如何产生宏观层面的影响等等。制药业在意识到了这一学科对药品创新的潜在影响后,彻底扭转了其认识论基础,开启了药物遗传学(Pharmacogenetics)和药物基因组学(Pharmacogenomics)研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也于1976年发布了《重组基因分子研究指南》来指导和规范相关实验室(314页)。在此背景下,制药公司不再执着于充满偶然性的发现之旅,而是积极推动重组基因研究,以发明取代发现。
作者以合成胰岛素的出现来强调这一时期制药业的重心转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胰岛素的生产逻辑是从牛或猪胰腺中提取,在发酵处理后用于患者治疗。1978年,美国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的科学家赫伯特·博耶(Herbert Boyer)团队成功将人类胰岛素基因插入细菌DNA,使其生产胰岛素(319页)。在与制药公司利来签约后,合成胰岛素畅销一时。此后,其他重组基因药物也相继出现,如人类生长激素、促红细胞生成素和单克隆抗体药物等等。
除了合成胰岛素,充当体育竞技兴奋剂的促红细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 EPO)或许是重组基因中最受关注的药物了。虽然这一药物原本用于治疗贫血,尤其适用于慢性肾病或癌症患者,但在制药业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地推动下,促红细胞生成素在运动员和教练群体中被广泛应用。九十年代初期,美国药监局在审批这项药物的时候,制药公司提供大量“临床证据”强调其安全性,而对滥用风险避而不谈。
无论是抗生素还是重组基因药物,其出发点都在于解决现有医疗知识体系内的疾病。换言之,制药业往往更加关注如何提供有更好疗效的药品来应对既有疾病。然而,精神药物的研发则彻底改变了这一逻辑。制药业的巨头们发现了一个简单且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创造疾病比解决疾病更加简单。
精神类药物时代:当疼痛变成疾病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疼痛被美国医疗职业视作特定疾病所带来普遍性症状,其本身不具有本体论意涵。例如,纤维肌痛(Fibromyalgia)在二十世纪一直被认为是其他疾病带来的症状,直到二十一世纪才被承认为“争议性疾病”(Contested Diseases)(Kristin K. Barker, The Fibromyalgia Story: Medical Authority and Women’s Worlds of Pain,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5)。在本书中,作者追溯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疼痛管理革命,并将其放置在不同主体——退休军人、患者群体、医生与制药业——构造的多主体空间当中加以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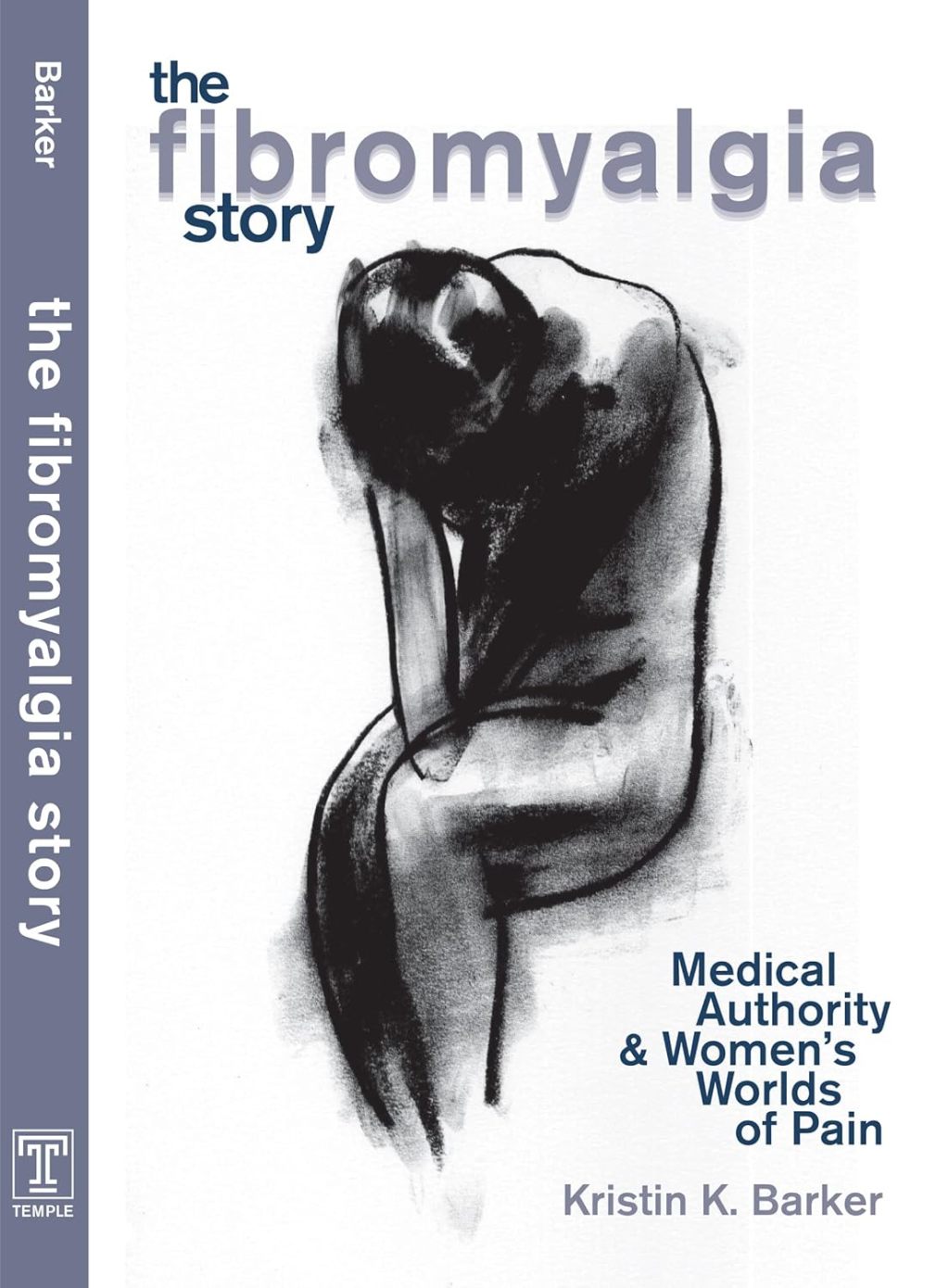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界定疾病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几乎一直是医生独享的权力,但伴随管理式医疗、制药业与健康社会运动的兴起,这一管辖权日渐被其他主体所侵蚀。疼痛管理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最佳例证。据作者所言,曾任麻醉师与职业摔跤手的约翰·波尼卡(John Bonica)是“挑战传统观念的领军人物”(341页),他在1974年组建了国家疼痛研究协会,并开始刊行《疼痛》(Pain)杂志。在他的推动下,医学顶级学术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开始引导人们反思生物医学对阿片类药物风险的看法。美国成瘾医学会借此机会鼓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会放松对阿片类药物的分配限制(345页)。美国疼痛学会也在这一阶段将疼痛视作体温、脉搏、呼吸频率和血压之外的“第五生命特征”。
当各方势力大力推动医疗革命时,普渡制药正在为推出阿片类镇痛药奥施康定焦头烂额。意识到医学知识正在发生变化,萨克勒开始将重心放在生产专业知识的群体身上:“花费数千万美元来为运动最前沿的医生、宣传团体和疼痛学会提供保险及资助。这些先驱来公司当讲师,获得了丰厚报酬。普渡制药和其他制药公司资助了医学院的课程、专业会议、公费旅游,甚至还赞助了以疼痛为重点的继续教育课程。”(347页)疼痛的概念被扩大到极其宽泛的范畴,医生们开始不遵循药品标签,而是大量寻求标签外使用(off-label use),门诊由此成为了瘾君子的购药渠道。
这一策略的直接后果在2002到2004年的监测数据中显露无疑。根据研究显示,奥施康定滥用案例已蔓延至全美百分之六十的三位邮政编码区域,其滥用率在八种阿片类药物中高居首位(与氢可酮并列),远超其他羟考酮制剂、美沙酮和吗啡。尤为讽刺的是,尽管普渡制药在2000年后紧急修改药物标签、增加“黑框警告”,但奥施康定的滥用率仍逐年攀升——这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农村和中小型城市尤为突出(≥5例/10万人)。这场以“医学进步”为名的营销狂欢,暴露了资本对专业知识的驯化。当普渡制药将“缓释技术”宣传为“低成瘾性”的科学突破(1995年的原始说明书甚至声称“缓释特性降低滥用风险”),它早已通过资助研究、教育项目和关键意见领袖,重构了医生与患者对疼痛的认知。
结语
如今,制药行业在社会医疗化进程中扮演着愈发关键的角色。上文以不同药品为核心,较为粗略地概括了美国制药业以药物滥用为代价,不断追求利润的残酷历史。在勾勒宏观变迁之外,《嗜血制药》还对不同时代制药业面临的选择和不断创新的营销方式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刻画,如沙利度胺滥用引发的灾难、奥施康定受害者家属的反击、萨克勒家族如何隐藏在数十家企业背后等等。这些历史片段不仅让我们对制药行业内幕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整个社会不断追求“健康”“规避风险”的医疗化趋势。
区别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社会,推动医疗化的动力不再集中于医生群体,而是转换到了制药行业。互联网、邮箱,甚至路边都充斥着各种药品的营销广告,它们无时不刻提醒着美国民众:你始终处于风险当中。曾经被视作医生管辖范围内的“疾病”(disease)如今也变成了弥散于整个社会的“不安”(dis-ease)(Kristin K. Barker, Mindfulness Meditation: Do-It-Yourself Medicalization of Every Moment,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982[106], pp. 168-176)。在此环境中,美国人花费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逐年增高,在2023年已经达到四点九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六分之一。在这一趋势背后,制药业始终发挥着极为强大的推动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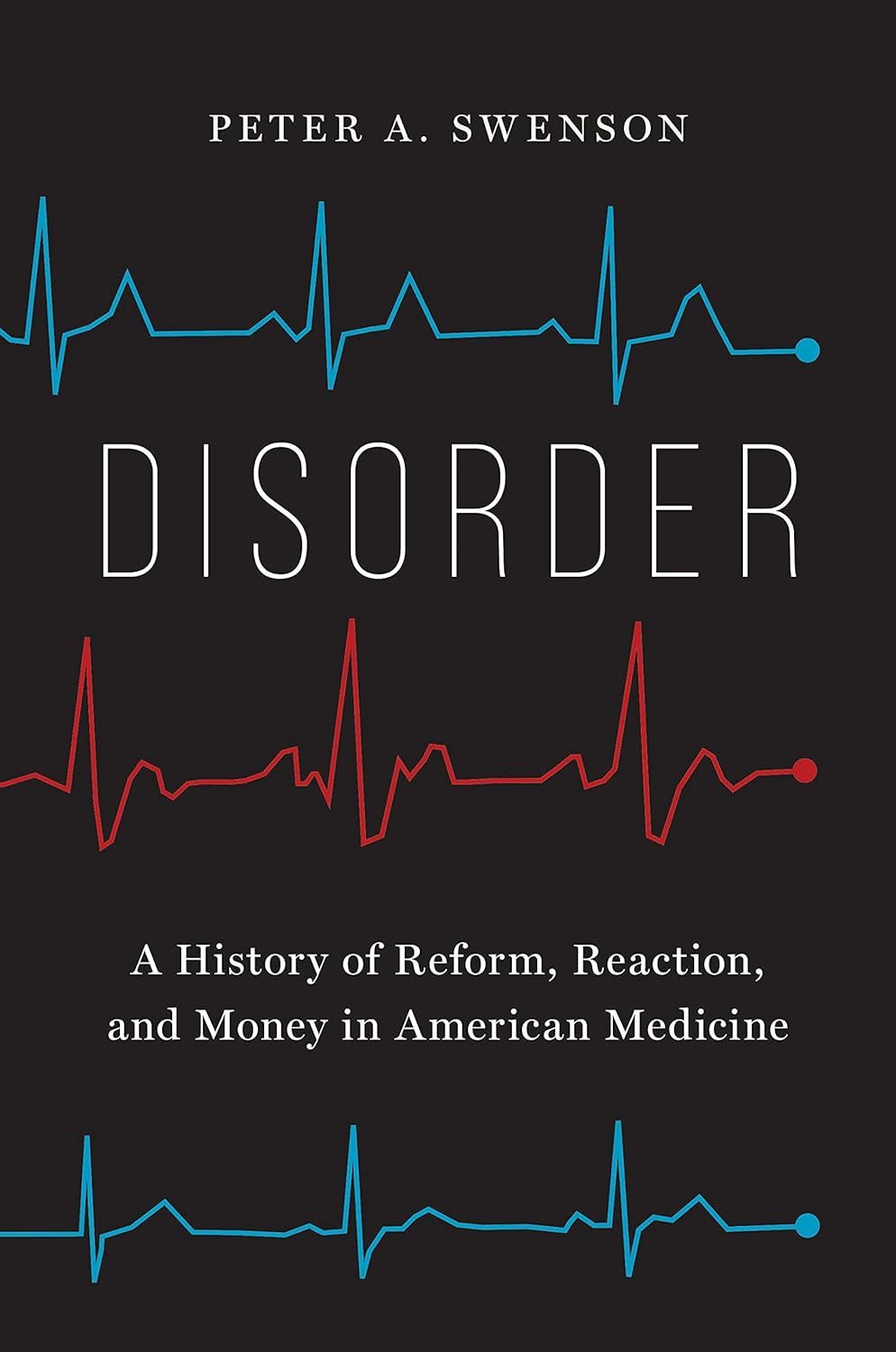
通读下来,《嗜血制药》在论述方面存在两点欠缺。第一,该书忽视了制药业与医疗职业、监管主体的动态互动过程。在其论述中,我们常常会看到一种叙事结构:当制药业采取行动之后,医生和监管部门才提供反馈,或消极服从或积极抗争。这一叙事往往淡化了后两者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更加积极的角色,例如美国医学协会在推动药品普及方面的积极程度不亚于制药行业(Peter A. Swenson, Disorder: A History of Reform, Reaction, and Money in American Medicin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第二,作者过度聚焦于制药业对美国社会的影响,相对忽视了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角色。一方面,鉴于美国生物医学在全球医疗保健发展中的主导地位(Howard Waitzkin,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at the End of Empire, Paradigm Publishers, 2011),制药行业如何推动全球生物医学化,进而扼杀传统医学的讨论较为匮乏。另一方面,该书未能揭示美国药企如何通过监管标准输出(如ICH指南),构建全球药品霸权。这种“中心-边缘”结构恰是当代全球健康不平等的根源。

作为一部历史纪实作品,《嗜血制药》通过揭示被遮蔽的庭审记录、内部邮件与受害者证词,为重构制药资本主义史提供了珍贵切片。它提醒我们,唯有将视线投向实验室之外,这部启示录的真正主角方才显影:一个由专利、医疗知识与资本共同铸就的利维坦,它诞生于实验室,却最终盘踞在整个美国社会的躯体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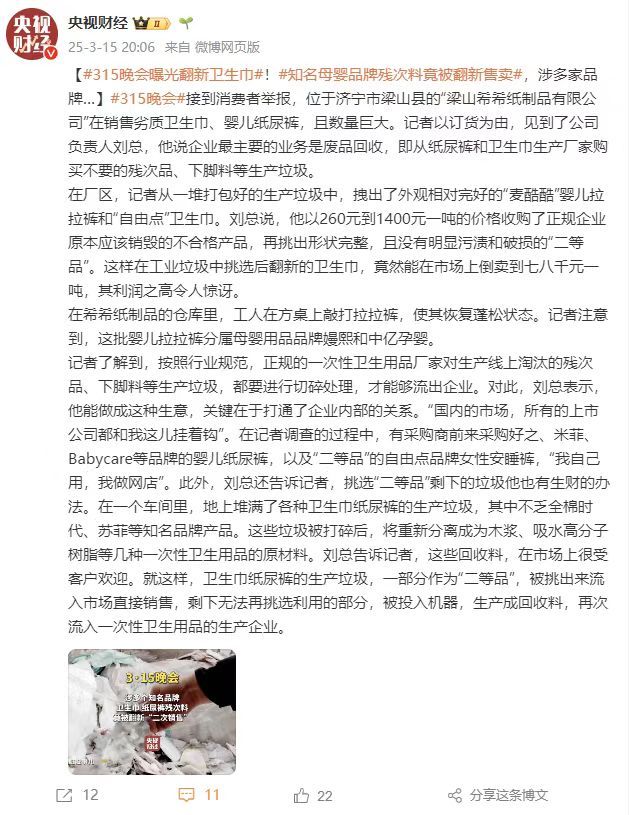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