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一周的星期六,我会给参与我研究的一些孩子上英语课。在这一天,我把孩子们分成了不同时间段的两个小组。我用心制订课程计划,让孩子们更多地参与游戏,尽量减少正式的教学。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自己成为孩子们的又一个学习负担,所以我尽量让大家共度的时光有趣起来。
添加微信好友, 获取更多信息
复制微信号
有一个叫艾比的9岁孩子很喜欢我的活动,她两个小组都参加了。她来的时候总是表现得很积极,所以当她在7月的一个星期六表现得情绪不佳的时候,我很惊讶。她一到就开始抱怨自己很累,说除了我的课之外她还有两门英语课要上,还有一大堆暑假作业要做。我试着让她高兴起来,说道:“如果你现在做完了作业,到了8月就可以玩了。”她反驳道:“8月我会有更多事要做!”
几个月后的一个周末,在中秋节的晚餐后,我去看望艾比和她的父母,这才对她抱怨的原因有了更多了解。艾比的父母一直在解释说,尽管夫妻二人在育儿上相互协作,但在特长班这个问题上两人持有不同看法。艾比的妈妈说道:“她爸爸觉得没必要去上那么多特长班。但我感觉,孩子之所以今天这么优秀,和上这些特长班有关系。”
艾比估摸着,在她9年的人生中,她肯定至少已经上了12种不同的课程。她尝试为我列出这些课程,不过马上就把手往空中一甩,说:“我自己都记不清了!”
随后艾比的爸爸开口了:“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我觉得在学习特长方面,就像专家说的,要按孩子的兴趣来,不要强行给他们增加负担。专家说孩子的天真单纯也是很重要的。可能创造一个轻松的环境,对她的身心健康有益,就已经很好了。可能她也没办法一下子吸收这么多特长班的内容。”
艾比的妈妈为自己辩护说,这些课程就是根据艾比的兴趣来选的。她让我问艾比之前那个周末发生了什么。看来艾比还记得那天的情形,她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周末。
“你那天怎么了?”妈妈要艾比说。
“那天的前一天是星期五,对吗?星期五晚上我去上了英语课。第二天早上我去上了书法班!然后下午我去上了你的课!”
妈妈很惊讶地问她:“你把去关老师那儿当成上课?”
“对。我确实把它当成上课!”
“但你不是说你很喜欢关老师教的吗?”
“对啊!但关老师教的单词我必须全都背下来!我一回家你就考我!我答不上来你就骂我!你会说,”艾比开始模仿妈妈,“‘哎呀!她都不收费了,你还不当回事!我再也不让你去了。’”
这番话自然让艾比的妈妈颇为尴尬,房间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但这一刻也很能说明问题。我其实一直因为自己也成了孩子们的课外班负担而深感内疚,但同时,我也确实为了让家长开心时不时地教孩子们一些新单词。我完全不知道艾比会在家被考这些单词。

艾比的妈妈赵海华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女性,她相信与女儿保持友谊很重要。她试着遵循专家的建议来提升女儿的主体性。例如,她曾给我讲过她把女儿从“小饭桌”小组里接走的故事(“小饭桌”是有人照看的孩子们的午餐小组,是学校老师为那些愿意并有能力支付额外费用的忙碌父母开设的)。“小饭桌”的老师总是抱怨其他孩子模仿艾比的一举一动。如果她吃了两碗饭,其他孩子也会吃两碗饭。赵海华说,艾比的老师普遍不喜欢艾比有个性这件事。尽管赵海华无法消弭学校文化与女儿个性之间的冲突,但她至少能把艾比从“小饭桌”接走,保护她的个性不被“磨平”。
赵海华总是自豪地谈起自己与女儿的亲密无间和母女情深,然而,中国考试制度的逻辑妨碍了她成为友好家长的努力。要想在严格的教育体制提出的要求与营造家庭“温暖”(用赵海华的话来说)之间取得平衡总是很棘手的问题。
尽管改革倡导者和政策制定者力图改变应试教育体制,但考试的地位依然稳固,每个人的未来就取决于高考和中考的表现。考试在中国儿童及家庭的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纵然中国的中产父母想按照专家建议去做,但随着孩子年龄增长、越来越临近关键的入学考试,确保学业生存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
以市为单位的中考决定了学生在国家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之后能否继续就读高中,以及就读什么样的高中(普通高中还是职业技术高中)。全国性的高考决定了学生最终将进入什么样的学院或大学(学术型还是职业技术型,“211”还是非“211”高校),以及选择什么样的专业。鉴于这两场考试事关重大,家长们认为就读合适的初中极其重要,因为这是学生准备中考的阶段,而中考之后则是学生准备高考的阶段。争取进入一所好名声的学校不只是执迷于社会地位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出于实际考量——确保有效的教学方法以及(对一部分人而言)确保孩子能有一定的生活质量。既然所有学生都参加同样的标准化入学考试,那么那些过度依赖复习课、布置大量家庭作业却又没有高升学率的学校便不受青睐。相比之下,在声誉好的学校,有能力的老师会用聪明的方法缓和学习强度。
在昆明,我结识的大多数家庭都希望孩子能上云南大学附属初中,该校的高中升学率每年都排名第一。这所初中声誉极佳,以至于人们常开玩笑说,云南大学才是这所初中的附属学校。作为一所民办学校,它向非大学教职工家庭每年收取7000元人民币,三年下来的教育费用共21000元。该校的入学选拔考试由语文和数学两个科目组成。根据《义务教育法》,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儿童都有权接受免费教育,在所在地的学校免试入学。但昆明的许多家长愿意“择校”,即在指定片区外找学校上。虽然21000元对普通的双薪家庭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家长们都争着把孩子送进云大附中。我结识的一个家庭决定不把女儿送去这所学校(尽管她被录取了),原因是每天的通勤时间太长。他们最后对这个决定颇为后悔,因为女儿如今淹没在海量的作业中,而且通过云大附中的入学选拔考试也实属不易。
学生通过在校学习做好准备参加标准化入学考试,这些考试强度很高,要在三天时间里测试学生三年来的多学科知识积累。学生必须学习掌握和死记硬背下来的材料(无论是几千年的史实和数字,还是无穷无尽的数学题——它们有些可能会出现在考试中,有些则不会)之多,对不在这个体制里长大的人来说简直难以想象。很常见的情况是,学校会用整个学期的时间来复习而不上新课,因为学生有太多内容要记忆。
当代考试制度植根于唐朝开始的帝国官员选拔制度——科举。这是一种全帝国范围内实行的标准化、择优录取的政府官员选拔机制。没有什么比金榜题名、晋升士绅阶层更荣耀的事了。参加科举的考生必须背下四十多万字的内容才能掌握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诸门课程,同时他们也会求助神灵并使用占卜手段来应对压力(艾尔曼[Benjamin Elman] 1991)(2000)。时至今日,诉诸迷信依然常见,足以体现标准化考试带来的焦虑和不确定:父母会在当地寺庙敬神,还会用“聪”和“算”的同音字食材(即葱和蒜)做饭。同时,学生会避免摄入任何不吉利同音字的食物或饮品,他们甚至会避免理发,以免“从头开始”。我认识的一个女生还会穿红内衣来求好运,这是她妈妈的主意。
高考出了名的折磨人,它是一种将学生推向人类忍耐极限的制度(任柯安 2011)。中考同样会带来焦虑,因为不同于高考(理论上一个人可以多次参加高考,直到考出满意的分数),学生只能参加一次中考。以2007年为例,中考一共包含六个科目:语文、物理、数学、政治/思想品德、英语和化学。总分是660分,根据预测,昆明重点高中的分数线在600分左右。参加考试后,考生需要在不知道自己分数的情况下,根据模拟测试的结果和往年各高中的分数线(分数线每年都会按照报考总人数和整体成绩的不同发生变化)进行估分,填报志愿。因此,入学考试都包含填报志愿这一额外工作,它需要有权衡各种因素和预测结果的能力。理想状态下,填报的志愿应与模拟考成绩相匹配,因为那些你可能考得上但在志愿中排名靠后的学校,可能不会接收你。
就中考而言,考试成绩高于学校分数线的可以作为公费生入学。而低于学校分数线10分的可以选择以择校生的身份入学,实际名额视指标而定。和在划定片区外上初中一样,择校生上高中的费用也很高。(这样的学生有时也称为自费生。)我没能核实到具体的费用,但我多次听到和读到,择校生需要为低于分数线的每一分支付1万元。
择校现象很普遍,这首先是因为人们对优质教育意愿强烈。好学校设置了很高的录取分数线,要求未通过的学生支付额外费用。其次,即使在同一个城市,学校之间的教学质量也参差不齐,所以尽管就读划片之外的学校要支付高昂费用,大家还是争着送孩子去更好的学校。这第二个因素与高收入社区还是低收入社区关系不大,而与中国的具体教育政策有关。好学校能将择校带来的收入投入其发展之中,与其他收入一道,服务于改善基础设施、招募一流教学人员,以完成学校知名度和地位的再生产。学校的发展又反过来强化了学校的教育资源,让高收费和低录取率更显合情合理。
支持择校的人认为这是一种亟须的市场机制,能让筹资渠道多样化,公众和个人皆从中受益。他们认为,择校现象只不过反映了大众对优质学校教育的渴望,这种渴望通过市场体制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得到满足,同时也弥补了国家资金的不足(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2005)。择校的批评者则指出,择校违反了教育公平原则,加剧了学校之间既存的差距,助长了腐败,还给民众带来了过重的经济负担(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2005;杨东平[2004]2006)。由于往往需要支付择校费才能把孩子送进理想的学校,家庭因而倍感压力,不得不利用手头的一切资源。由于入学考试成绩与要不要支付数万元额外费用直接相关,学生因而心理压力倍增,必须刻苦学习。由于评估学校和老师根据的是学生的升学率,提供教育因而变成了狭隘的“应试教育”。
以应试为中心的教育体制带来的一个意外后果在于,学校和老师倾向于关注有前途的学生,而“歧视”其他学生——不公正地对待他们,让他们留堂、停课,开除他们(Man Qimin[1996]1997)。这类歧视现象在享有盛名的精英重点中学尤为突出,不过它早在小学就开始了。我常听到这样的故事:有孩子被施压或被要求离开学校,有家长因孩子与小学主科老师有矛盾而将孩子转校。对学生而言,一种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就是老师不再关注他们了,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教师承受的压力和面临的竞争。在昆明,从小学到中学,班级规模都相当庞大。老师要引导足足50-70名学生迈向成功,这让老师也感到负担沉重,对学生的越轨行为没什么耐心。
我之所以强调择校问题,是因为在家长看来,正是择校这一中国应试教育的具体表现,成为他们面临的最紧迫的道德问题和实际问题。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过上好日子,这意味着确保他们有朝一日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成为受人尊敬的人。为了能让孩子找到好工作,家长必须确保他们踏上通向好大学的道路、取得有分量的学位。为了让孩子踏上正确的道路,家长必须通过补习班和日常监督来提高孩子的应试能力,同时想办法负担进入好学校的费用。如果孩子与老师发生冲突或产生误解,家长必须要么帮孩子重获老师的好感,要么寻找新学校,因为在普通家长看来,与老师的关系好坏能决定学业的成败。
放眼全球,焦虑是中产的内在组成部分,一代代人都必须通过教育成就来确保中产身份地位(克雷默-萨德利克[Tamar Kremer-Sadlik]和古铁雷斯[Kris Gutiérrez] 2013)。和美国中产阶级母亲一样(尽管课堂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中产母亲也积极干预和学校有关的不利状况(拉鲁 2011)。在中国,考进好学校的热潮也与艾利森·皮尤在加州湾区的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中发现的“铺路消费”(Pathway Consumption)相类似。“铺路消费”是为了创造那些能塑造人生轨迹的机会,以及确保“舒适”的学习环境(2009)。因此,从比较视角来看,中国中产父母的强烈焦虑并不是完全独有的现象。全球经济鼓励个体“将自己视为可资管理和发展的人力资本投资组合”(安德训 2013),并期望个体和家庭能吸收系统性矛盾的“冲击”(15)。各国的就业市场十分不稳定,毕业生失业的阴影笼罩着许多国家。通过对教育投入金钱和精力来投资人力资本的做法虽然不能保证回报,但至少是中产家庭掌控之内的事。
本文摘自《不确定的爱:当代中国育儿的希望与困惑》,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标题为后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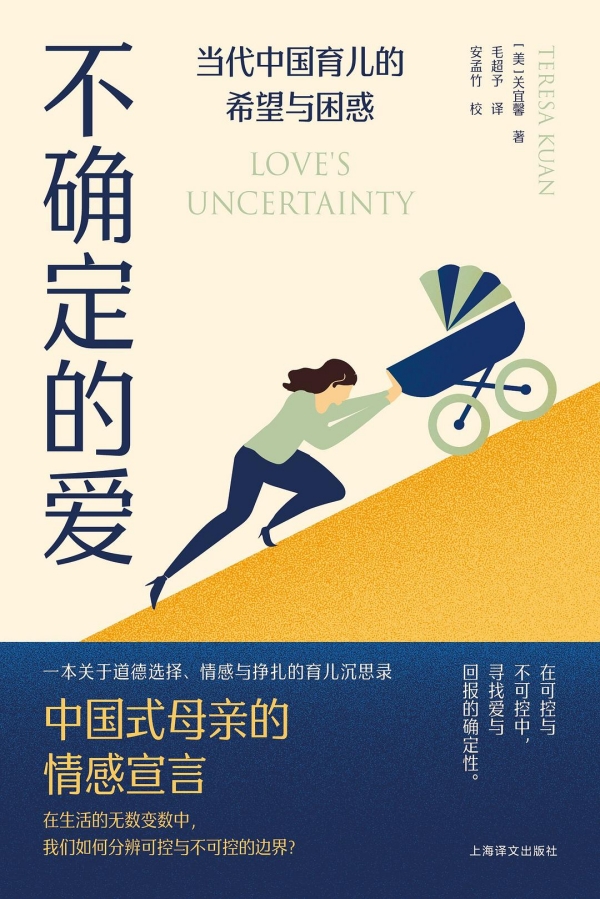
《不确定的爱:当代中国育儿的希望与困惑》,【美】关宜馨/著 毛超予/译 安孟竹/校,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1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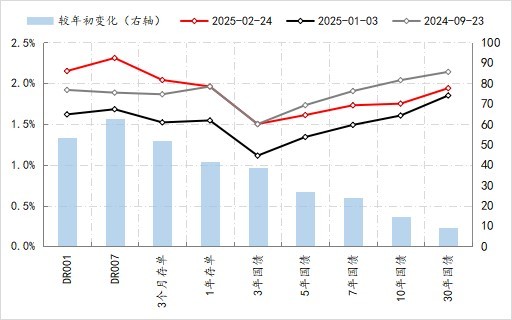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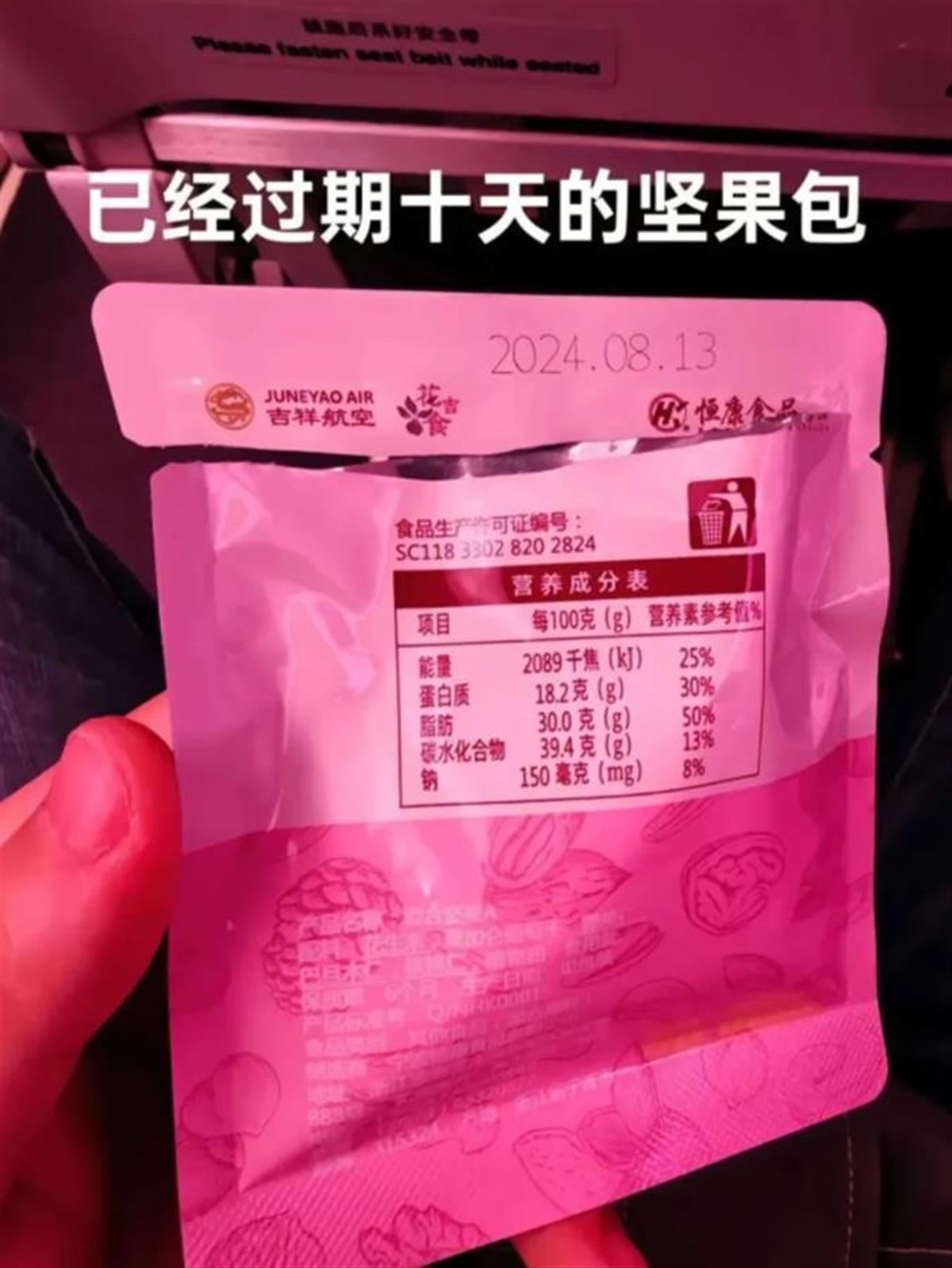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