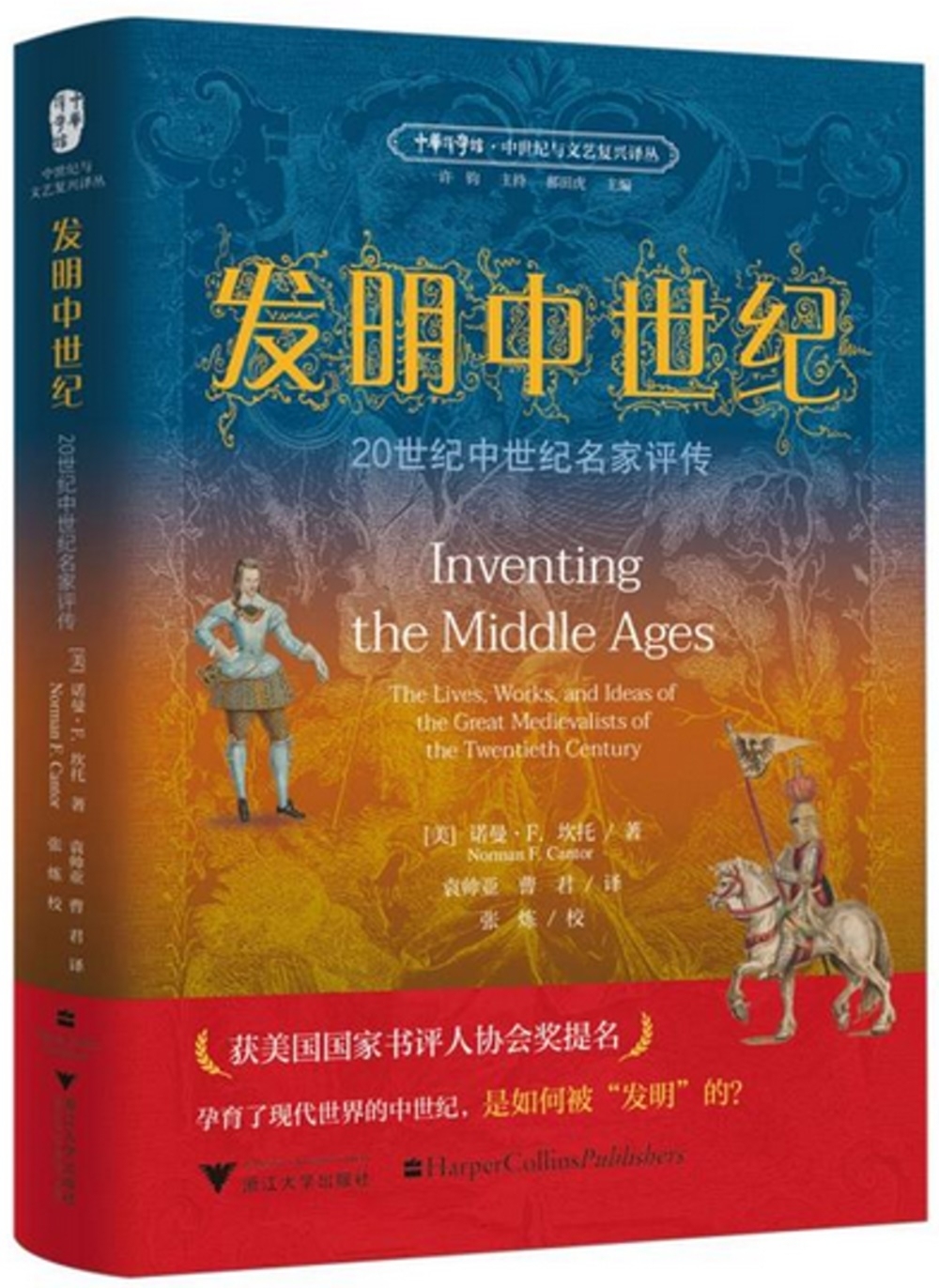
《发明中世纪:二十世纪中世纪名家评传》,[美]诺曼·F. 坎托著,袁帅亚、曹君译,张炼校,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420页,88.00元
添加微信好友, 获取更多信息
复制微信号
我最早知道诺曼·坎托的《发明中世纪》,是通过英国学者马库斯·布尔(Marcus Bull)的《思考中世纪》(Thinking Mediev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Ages, Palgrave Macmillan, 2005)。当时电子书籍尚未普及,无法阅览原书,但一直听闻书中“学界掌故”极多。等到去利物浦读书的时候,从图书馆里借阅的第一批书中便有这本。
早年,我曾在豆瓣上写过一篇个人色彩浓厚的“读后感”。友人提议,这本书应当翻译成中文。如今中译本付梓,重读之际仍感慨万千。这本“八卦”密度极高、公开臧否人物的书,为作者坎托带来了不少麻烦。当年的一些故旧友人对他将诸多私密事与所谓“妄加揣测”公之于众颇有微词。也有人批评他过于关注学者的个性及其主观偏见,认为这简化了复杂的知识成果,使之沦为个体心理的投影。
若仅将此书视为“谈资”的资料库,未免失之偏颇。《发明中世纪》是一部以传记形式为骨架、以学术进展与方法论批判为经脉的知识史著作。书中描绘了中世纪研究从十九世纪末逐步建立的宏大画卷,并深入探讨了若干中世纪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者在学术思考背后的个性与意识形态。这种汪洋恣肆、臧否人物的写作风格,也将坎托本人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被放逐者的坎托
诺曼·弗兰克·坎托(Norman Frank Cantor,1929.11.19-2004.9.18)是一位加拿大裔美国中世纪史学家。他出生于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温尼伯的一个犹太家庭,在家乡完成大学教育后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之后又以罗德学者的身份在牛津大学的奥里尔学院学习一年。在牛津期间,他的指导教师便是著名的理查德·威廉·萨瑟恩(Richard William Southern)——我个人最喜欢的二十世纪英国中世纪史学家。之后,他重新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师从美国中世纪研究奠基人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的高足、著名中世纪史学家约瑟夫·R. 斯特雷耶(Joseph R. Strayer),获得博士学位。
坎托的早年研究主要集中于中世纪盛期的英格兰,他一生唯一的学术专著《英格兰的教会、王权与世俗授任:1089-1135年》聚焦于十一到十二世纪大转型时期的英格兰政教关系,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然而,坎托的天性似乎更热衷于宏观历史叙述,即便是在学术论文中,他那种大开大合的风格也显而易见。坎托文笔极佳、视野恢弘,其所撰写的教材和通俗读物常常成为畅销书。他在1963年首版发行的《中世纪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the Middle Ages),到二十一世纪初已经卖出了超过一百万册,几乎成了英语世界对中世纪历史感兴趣之青年学子的必备参考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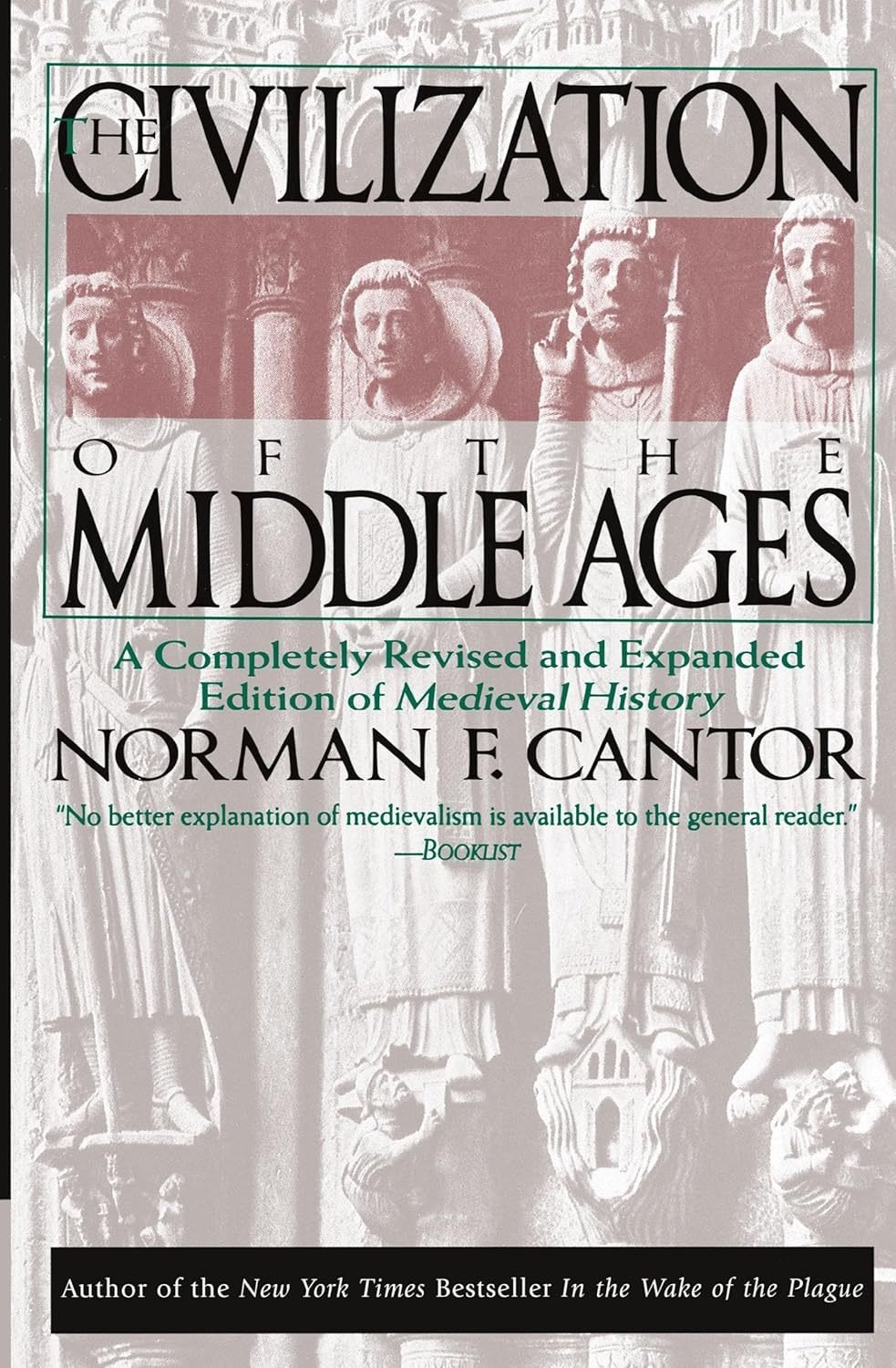
坎托著《中世纪文明》
然而,在学术圈内,对坎托的学问水平及性格的评价褒贬不一。早年,许多人曾认为他必将成为斯特雷耶的接班人。然而,在普林斯顿任教三年后,他因种种原因逐渐被主流学术圈边缘化,之后辗转于哥伦比亚大学、布兰代斯大学、宾汉姆顿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和纽约大学等多所高校,直到1999年退休。关于他自己与若干“学界大佬”和“学界主流”之间的恩怨情仇——例如,前些年因新冠去世的中世纪研究“巨擘”吉尔斯·康斯坦博(Giles Constable)因家世优越抢占了本应属于他的哈佛教席——这类故事在2002年出版的《发明诺曼·坎托:一个中世纪学者的告白》(Inventing Norman Cantor: Confessions of a Medievalist, ACMRS Press, 2002)中有非常深入的剖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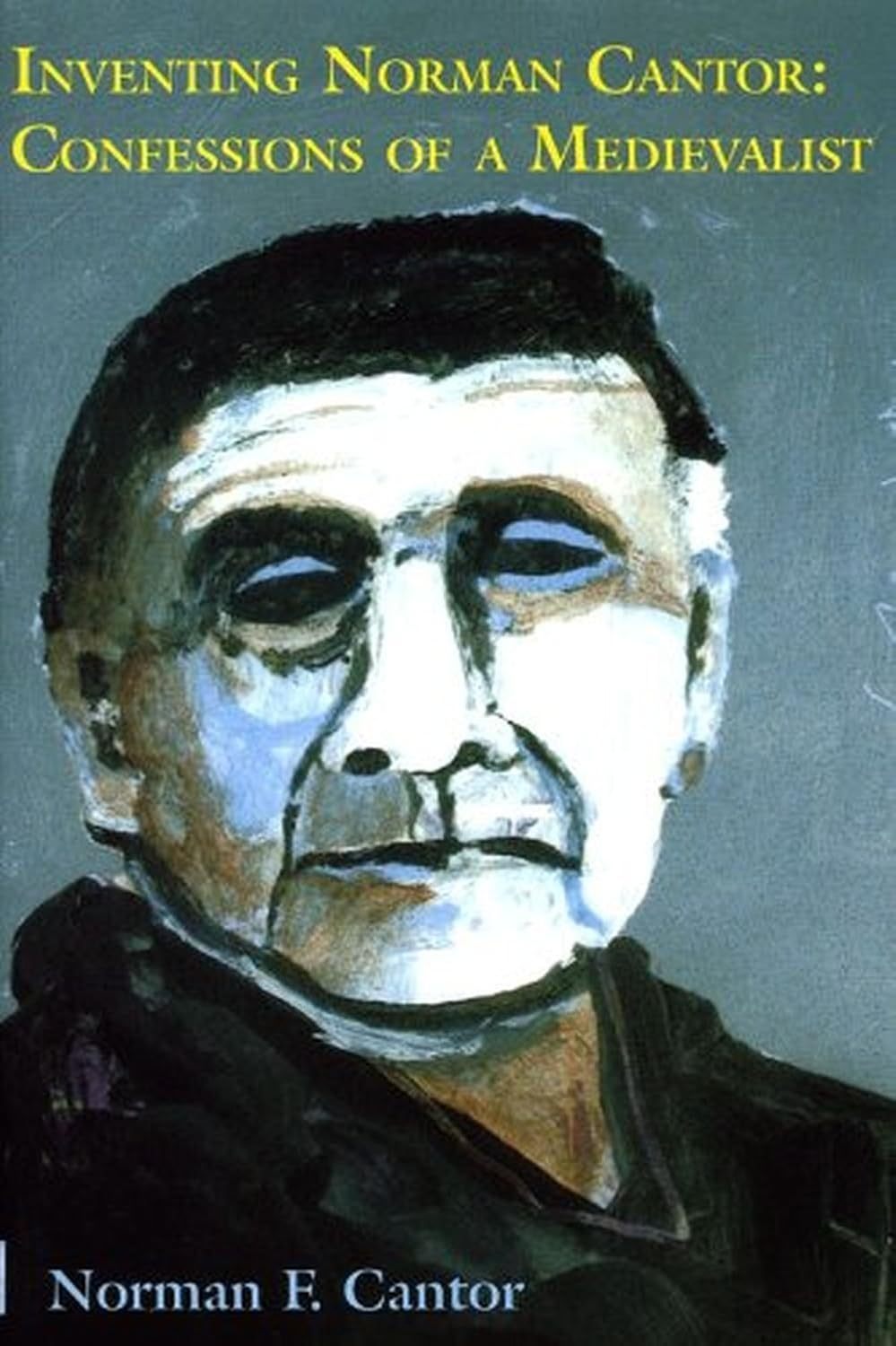
《发明诺曼·坎托:一个中世纪学者的告白》
这部作品出版两年后,坎托便在迈阿密的家中因心衰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在他去世二十年后,那本使他名声大噪的《发明中世纪》被翻译为中文出版,让重洋万里之外的异域读者也可以感受他挚爱的中世纪研究。
时代与历史书写
在欧洲文化传统中,历史学的地位远不及在华夏文明中那般崇高。我们对欧洲古代世界的认识大多源于十九世纪,而对中世纪的理解则主要形成于二十世纪。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们率先打破了启蒙运动以来贬低中世纪的论调。然而,尽管他们感情充沛,却普遍缺乏足够的学术素养,也多未掌握探究高深学问的手段。
坎托在本书的开篇写梅特兰,正是为了给中世纪的科学性研究寻找一个“鼻祖”。他将梅特兰视为英国“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在英国史学界和英美法律学界,梅特兰都是一位被尊奉为圣徒般的人物。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历史学的发展才逐渐显示出推动学术革命的灵感和力量,而中世纪研究更是最后才从尘封的档案与顽固的“黑暗中世纪说”中破茧而出的。中世纪全盛期的成就及其特征、形成原因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副作用,始终是二十世纪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正因如此,我在十年前开始探究“十二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发展演进,这个选题的灵感也萌发于和徐善伟老师一起在利物浦抽烟聊这本书中“八卦”的过程。
坎托的中心论点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世纪”,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被发明”出来的。史学家的判断、倾向以及基调必然与他们所处时代的风气密切相关。这些学者在描绘中世纪的历史时,无一例外地带着自己的文化背景、民族认同、宗教倾向与政治意识形态。如果一部学术作品中缺乏作者的愤怒、怜悯和灵魂共鸣,它大概率不会成为一部优秀的作品。坎托的论据正是这些学者的传记与他们不朽的著作:个人生活总是与学术生活交织在一起。作者本人的经历、情感乃至偏见在他的著作中都会有清晰的体现。于是,我们就看到在法国学者的笔下,“十二世纪文艺复兴”成为了欧洲中世纪文明最光辉灿烂的篇章,而这辉煌时代的文化中心便是巴黎,整个欧洲都要唯法兰西马首是瞻。在英国学者笔下,《大宪章》和宪政的胜利是英格兰带给欧洲最好的礼物。此外,中世纪学者在训练过程中,非常容易将中世纪和现代文化之间作比较与关联,毕竟当今西方社会的主体价值观和社会运作框架都是从那个时代发展而来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中世纪历史某个方面或领域的侧重,常常与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热点高度契合。那些在著作中过分赞美中世纪教会特权以及王室权威的人,在生活中也常常是推崇君主制和政教合一的潜在狂热分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必然地就是政治的。
梅特兰等人认为,中世纪是一个始终处在混乱边缘、智力产出有限的时代,他们希望自己的时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的布洛赫及后来的年鉴学派,则希望通过研究历史消灭等级制度和社会不公,尽管他们自身的学派发展史也充满了“巴黎与外地”“大佬嫡系与外来者”之间等级不公的血泪。潘诺夫斯基、库尔提乌斯,以及施拉姆和康托洛维奇等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十九世纪德意志唯心主义的后裔。其中一些人将无与伦比的中世纪思想变成了现代社会危险变革的反射镜,另一些人则希望通过回归古典主义和基督教神学共同构建的中世纪主义,抑制过于激进的现代性(158-160页)。坎托批评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批德国中世纪学者,认为他们作品中充满了浪漫化的民族主义。他们试图构建一个英雄化的中世纪形象,其目的正是彰显德意志民族的伟大、鼓舞德意志民族的情绪,最终不仅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更酿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惨烈的历史事件。
再看“与欧洲分享着同一个过去”的美国,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哈斯金斯的“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理念带有极为强烈的威尔逊风格的进步主义色彩,体现出一种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至上的精神。哈斯金斯本人的性情、生活、成长经历乃至心理特征,也与威尔逊有诸多相似之处。从许多方面来说,哈斯金斯那一代学者实际上就是将美国例外论的变体,移植到了“盎格鲁—诺曼—法兰西”的中世纪国家建构的研究上(200-201页)。哈斯金斯具有极强的使命感,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源于演讲稿,所预设的读者也是公众而非专家。这是世俗学者的“布道”,是向大众传授人文主义理想的威尔逊主义传统。因此,其研究结论不仅来自中世纪文献,更深深植根于个人生活与现实处境。
学术界的背阴面
坎托这部作品最吸引人之处在于他的直言不讳,以及对学术界若干秘辛的揭露。这些故事有的源自他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有的则出于道听途说。坎托的文笔带有强烈的文学色彩,描写梅特兰与菲利克斯·利伯曼的初次见面,以及施拉姆与康托洛维奇的少年聚会,寥寥数言就能将读者带入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那种弥漫着煤炭燃烧味道、耳畔响起内燃机轰鸣的历史场景中。
二十世纪的学术世界可以说是一个“圈子社会”。梅特兰属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该团体的主要人物包括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其姊妹艺术家凡妮莎·伍尔夫及其夫婿,还有对二十世纪经济学和国家经济政策影响深远的约翰·凯恩斯。而恩斯特·施拉姆和康托洛维奇则分别属于阿比·瓦尔堡和斯特凡·格奥尔格的圈子。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牛津的C. S. 刘易斯、J. R. R. 托尔金等人也组成了淡墨会(Inklings)。在这些松散的组织里,学者们讨论自己的读书心得,相互朗读和评判彼此的文稿,逐渐形成了学术圈内部的联盟。
不久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把犹太裔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葬入先贤祠。布洛赫是法国二战抵抗运动中,唯一一位牺牲的著名学者。令人唏嘘的是,在他为国捐躯时,著名女权主义者西蒙·波伏瓦还在纳粹控制下的巴黎广播电台领取不菲的薪水,而担任戴高乐政府文化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则在他情妇的地中海别墅中畅饮窖藏美酒。与此同时,对于布洛赫的子女们,父亲忽略了他们的感受和生活,使他们陷入贫困和无助之中。
坎托对学术界的现状充满愤怒,他尖锐批评学术界的“近亲繁殖”“圈子化”“封君封臣制”“学术官僚体系”等现象,直言这些弊病几乎可适用于任何国家(参见施爱东:《蛋先生的学术生存》,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
许多学者都是从童年或青春期起便对语言、历史以及神秘的宗教抱有浓厚兴趣,继而放弃追求财富和权力,仅靠教授的微薄薪水过活。其学术创造力的巅峰多集中于四五十岁,之后往往不再或难以从事重要的学术工作。坎托用辛辣的笔调描绘出这样一代学者:他们凭借某种学术阐释获得成功,地位逐渐攀升后,不但不再自我批评或修正过往研究,反而谨小慎微、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新教条,仅允许下一代学者中的“阿谀学舌者”进入他们所掌管的“众神之殿”。
作为犹太人,坎托对纳粹主义深恶痛绝。他明确指出,即使是那些后来受到迫害的犹太裔教授,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也曾支持“强人政治”,幻想一位强大的领袖能带领德国恢复“民族的注定伟大”。坎托毫不留情地批评这些德国教授,认为这些人并未真正受到历史、法律和正义的审判。而且,这些人不仅或隐或显地认同了纳粹所宣扬的理念,从本性上来说更是“胆小怕事、懒惰自私”。
此外,坎托对自己亲炙过的学者也同样不留情面。例如,他在牛津大学做访问学生时的导师理查德·威廉·萨瑟恩被他视为“过去与未来之王”,但对萨瑟恩的“牛津式”傲慢、不谙德文以及对中古德意志极具偏见颇有微词。坎托认为,萨瑟恩的《中世纪的形成》在自己和许多读过这本书的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接受了理想的召唤后,我们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但是,萨瑟恩从未利用自己的天赋、职位或学缘来对年鉴学派形成制衡,因为他害怕自己的作为有悖于英国教授的传统。然而,在坎托看来,正是因为萨瑟恩最终选择不挑战学术界,才导致今天的中世纪研究每况愈下。用坎托自己的话来说,如今“只剩下布洛赫的门徒们在欧美统领这个领域,因为他们有资源和组织”。
在坎托出版这本书的时候,萨瑟恩仍然在世,并正全力编写他的最后一部巨著《经院人文主义与欧洲的统一》。我们无从得知,萨瑟恩在看到坎托对自己的评价会作何感想。在他未竟的遗著中,我们也只能从书名中隐隐感受到他最后一搏的微弱力量。往好了说,萨瑟恩仿佛是一位完全遵从内心召唤的中世纪圣徒;可往坏了说,他何尝又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既得利益者呢?
中世纪能为今天带来什么?
中世纪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恒定性”,这并非意味着那个时代毫无进步,而是说西方文化在时空中表现出高度的统一性。十二世纪的作者所表达的一切,仍可追溯到在公元三百年前后逐渐形成的思想体系。对康托洛维奇以及库尔提乌斯等人而言,正是但丁将“一种发酵剂”融入到中世纪西方传统中,使文化的稳定性和绝对的思想延续性开始发生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与后现代社会的碎片化和无序形成鲜明对比,中世纪的核心特征是将一切融为一体。尤其是自十二世纪以来,中世纪的学者、文学家和诗人都成为了各种知识体系的建构者和统筹者,以其博学和包容,在多样化和不稳定的环境中传承着伟大且濒临失落的学问。这样的一种处境,很难不让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产生共鸣乃至同情。
中世纪的人们与我们拥有相似的情感与焦虑,却无需背负现代社会沉重的“官僚—司法—技术—税负”枷锁。坎托认为,中世纪发展出的王权理念是一门独特且精心建构的学问,是一个富有永恒创造力的有机体。中世纪的王权将罗马的、基督教的、德意志的和拜占庭的种种资源,不断地加以重组、探索和扩展,这样的一种组合能在极边缘的地方体现出巨大的自发创造力,还能坚守高度功能性的内核。
中世纪有拥有巨大的疗愈力量,正如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将其视为面对工业化和军国主义恶魔的避难所。这种吸引力最直观的表现便是带有浓厚“中世纪主义”风格的奇幻小说与影视作品。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中世纪是一个迷人的影子、模糊的替身、可以相互连接的他者,是我们梦想、忧虑和秘密的分享者。
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对于中世纪或许还需要更新的解读。除了学术研究的积累,学者们似乎也需要一个特定的时代氛围来点燃灵感。传统的历史研究难以根本改变我们目前对中世纪政府、社会和经济认知的基本轮廓,但通过对中世纪艺术、文学和哲学的探索,我们或许在二十一世纪能够更深入地破译中世纪人们的心灵。中世纪艺术的强大思想凝聚力来源于创作者对传统的延续,而非刻意追求突破性创意。他们在既定母题的框架下呈现信息,以确保观赏者一目了然。在这样的背景下,微小的变化往往预示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所建构起来的权威性知识体系都是针对欧洲中世纪的,这些理论、方法都不足以对其他区域的“中世纪”社会加以概念化。
对于在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有多少人未曾听闻或阅读、观看过《玫瑰的名字》《魔戒》《哈利·波特》《权力的游戏》呢?这些作品通过新兴媒介的传播,使中世纪精神的某些特质得以持续影响我们对世界运行法则与真相的理解。特别是托尔金和刘易斯,他们的奇幻作品与学术研究之间存在着一条清晰的脉络。正是通过这些作品及其影视化改编,中世纪的形象深深嵌入了当今世界的文化版图。
无论大家是抱着猎奇心态,还是探索学术史,这本融合传记、知识史和方法论批评的书一定都不让令人失望。我盼望能有更多的青年学子,借此“猎奇之旅”的契机,走进光明与黑暗并存的中世纪研究领域。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