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扯:相对剥夺感的控场
添加微信好友, 获取更多信息
复制微信号
《一跃而下》囊括了七篇小说,七篇各有各的人物和故事,但整本集子的母题意识浓厚,各篇之间独立存在,却又殊途同归,作品里都有一个被相对剥夺感操控的“我”,贯穿着每个故事的进行。
我们这代人的绝大多数,在物质条件上不至缺乏,而顾文艳书里那些人物——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同龄人们,应该更不太会有这种物质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生长经验。但相对于上一代的“均衡匮乏”,这一代的问题却从物质上的丰足改善演化到了精神上的相对剥夺。更可怕的是,这种剥夺感的背后,可能是相当正面的“努力”与“上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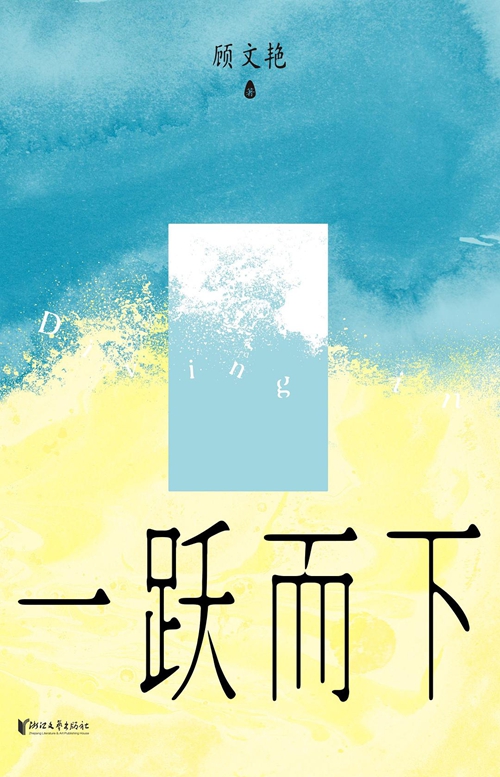
《海怪》里安排的这位“彭欣阿姨”,像很多我们熟悉的清高、优越、生活圈层同质化严重导致某种偏执的中年知识女性的分身。她居高临下、客气而疏离地对待“我”。《仍然活着》里,“我”是一个纠缠于普通的事业、平凡的家庭的女性角色,作为对照面的祝力文,这位少年时代的朋友,进化出一种几乎浮夸的强势、聪明、貌美、多金,令“我”从她那里感受到了显而易见的压迫。《恩托托阿巴巴》中,“我”因为受困于现代人糟糕且无解的邻里相处环境,采取了“以暴制暴”的方法,叫来一帮同学在家开party,意在对抗楼上的噪音。但是在这场三个人聚会上,就连细微到对于酒水的知识储备,都暗示着每个人生活轨迹的落差。《人工湖》贡献了本书的书名“一跃而下”,“寻泽”在一场朋友聚会上旁观朋友家典型的中产生活套路,但是她自己面对着一整面光明美好的窗外的人工湖,却正被来自身体上的女性困境绑缚,她迫不及待渴望找到一个可以真正一跃而下、可以冲刷自己的“人工湖”。
母女关系经常会透过各种千奇百怪的故事呈现出世界上最复杂的情感关系案例。每个人都不可避免遭遇一些扭曲着塑造了我们人格的并不太美好的经验,糟糕的是,母亲这一角色有时候会重度参与这个改造工程。许多女性下意识想要逃避成为自己的母亲,但是会在某一天避无可避、在自己身上发现母亲的影子。顾文艳是坦诚的,她的“自我暴露”从自序就开始了,她说“我妈妈是一个很有韧性的人,意志强大,偶尔强大到能扭曲现实。”“我天生争强好胜,遗传了我母亲的激烈、易怒和坚定。”——这让人几乎觉得作家的母亲是这本小说集得以面世背后最大的那个“因”,而这位“母亲”也会不时化身为小说里轻描淡写的一个配角登场。顾文艳说有很多话想说,于是在自序里干脆利落地总结了自己一路走来的过程。母亲一手将她推到写作的道路上,安排她初中离家进了一所名校,同学们“非富即贵”,于是日后逐一成为《一跃而下》里的素材来源。
相对剥夺感,从这里就开始了,而且越是向上向好的人,这种剥夺感就会越严重。作家说自己在耐力型体育运动以外的赛场上,“输得气急败坏,嚎啕大哭。”“我拼尽全力的赛跑是多么徒劳,像从一堵墙跑到另一堵墙。”所以她在二十年后回望一切时总结道:“我所做的一切,最终是否只是中学时代的循环往复,只是在一个比校园稍大一点的社会场域里,依赖个人先决优势,继续争夺资源、斤斤计较的游戏?”
创作取材于生活,生活是由经验组成的,人是被过去的经验塑造的,而这种经验常常并非是美好的,而是掺杂着创伤的成分。个体经验可以被深藏,但顾文艳似乎选择了一种坦率的暴露式疗法。这实际上是一本由人及己的书,作者在这本书中探索,坦露,寻求可能的疗愈。
勇气:被坦诚的病态
七篇作品里的人物,多多少少有些被生活逼到了临界点的味道,有人面临生理的困境,更多的则是精神上的“病”。《海怪》里的“我”,压抑和不快乐显而易见,而随着故事发展,属于吕陆海的部分似乎走到了一些更加激烈的怪力乱神的轨道上,他每天用一个奇形怪状的无人机去湖边监测水质,从钓鱼人的杆上救下了一条怪鱼后,选择在林荫深处的高档别墅养鱼。“一开始它住水池里,后来换成了鱼缸,更大的鱼缸……最后他买了水族馆里的深水大鱼缸,把房子的地下两层都打通,封砌地面”——十分奇幻,又确实是深嵌于现实的故事场域。
《恩托托阿巴巴》开头写道:“我真的崩溃了,楼上的小孩子又在来回跑。咚咚嗒嗒咚咚咚,铛铛铛咚。形状各异的踏步声落在我脑袋上方的不同位置,宣告不同种童真的轻重缓急。三个娃一起,短程赛跑,从这头到那头,反反复复。”同篇中的duke,出身优越,经历光鲜,却将自己封闭起来长达十年,用一句古怪的“恩托托阿巴巴”作为和这个世界勾连的唯一暗号。一切的根源,在于他当年在非洲因为自己的软弱和恐惧,对朋友的见死不救。他选择用用有形的车保护了自己的肉体,代价是十年的自我封闭和失语。“duke失语了。一整个月,他没跟任何人说话,自我介绍?怎么可能呢。他顺利完结了一整个月的实习,没说话。……因为忽然间,duke的眼皮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拨开。他的身体被重新陷进沙发,一只手再次伸进已修,另一只手再次用手指绕住衣袖上那根没扯完的线头。线头终于断了一处,啪叽,这声音只有拔线的他和看他拔线的我能听到。他的目光挪向落地窗边,米色泛黄的窗帘是一摞摞堆叠的皱纹。‘恩托托阿巴巴’”。从精神的逃避演化到物理的封闭,最后再反噬表现为精神的病态,这未尝不是对精神救赎的追寻,过程充满了自我的粗糙磨砺。
张力:文字内里的力量感
这本集子的文字张力来自于没有彻底走到“迹类疯迷”之前,正常人与不正常生活之间的撕扯、角力。
作家显然会部分化身为书中的“我”,作为故事行进的线索,在各种充满虚无感的人物和情节描写之间制造一种充溢全书的撕扯感,并且因此具有感染力。作者的勇气是站在这场角力的上风口的。就像她在序言中先行自陈的那样,她对生活是不愿意认输的。但她的文字并不张扬,说着精神拉锯的故事,依然十分冷静。
作家受到过的良好且完整的外国文学系统教育隐现于她的写作中。《世界已老》一篇,显然来自她的《浮士德》经验。作者以全文独白的形式,向一位名叫“一方”的倾听者讲述了“在淮海路碰到梅菲斯特”的过程。“梅菲斯特”消失在淮海路狭小街巷的一个小酒吧里,正当作者怀疑自己见到是否梅菲斯特时,消失的人瘸着腿,用一个拖把灵巧地几乎是安静地消灭了一个意外产生的火球。
现实和超现实手法之间的这种转换也出现在《海怪》中,从一开始住到清幽的郊区别墅,到隔壁仿佛林中仙人一般冒出来的一对“高尚夫妻”。等到“吕陆海”和他的怪鱼出现,后半段的故事张力,超现实的味道更是如浪一样叠上来。吕陆海在这个空间里将小小的怪鱼养成“我”日后记忆里一个似真似幻的梦一般的片段:“透过挡风玻璃,我能从后排看到一只庞大的、发光的怪兽正在前方的公路上缓缓穿行——它前后长着四条腿,身体狭长,大概有一辆车那么长。形状如刀鱼 ,嘴若长矛,树枝状的触须垂在安静的鱼唇上。塔通体透明,脊背在城郊的路灯下明亮地闪烁……我认出那是吕陆海和他的同伴,一前一后扛着他们的鱼,像两个扛着船艇的赛艇运动员。背鳍和脊骨持续发光,像个奇迹”。小说虽然篇幅不长,却在节奏上有不动声色的加速,有起伏回落。
我和顾文艳算是同代人,对于共享一个时代的人来说,阅读的过程是辨认那些平施于每个人的痛苦、纠结、压抑的过程,也是自我观照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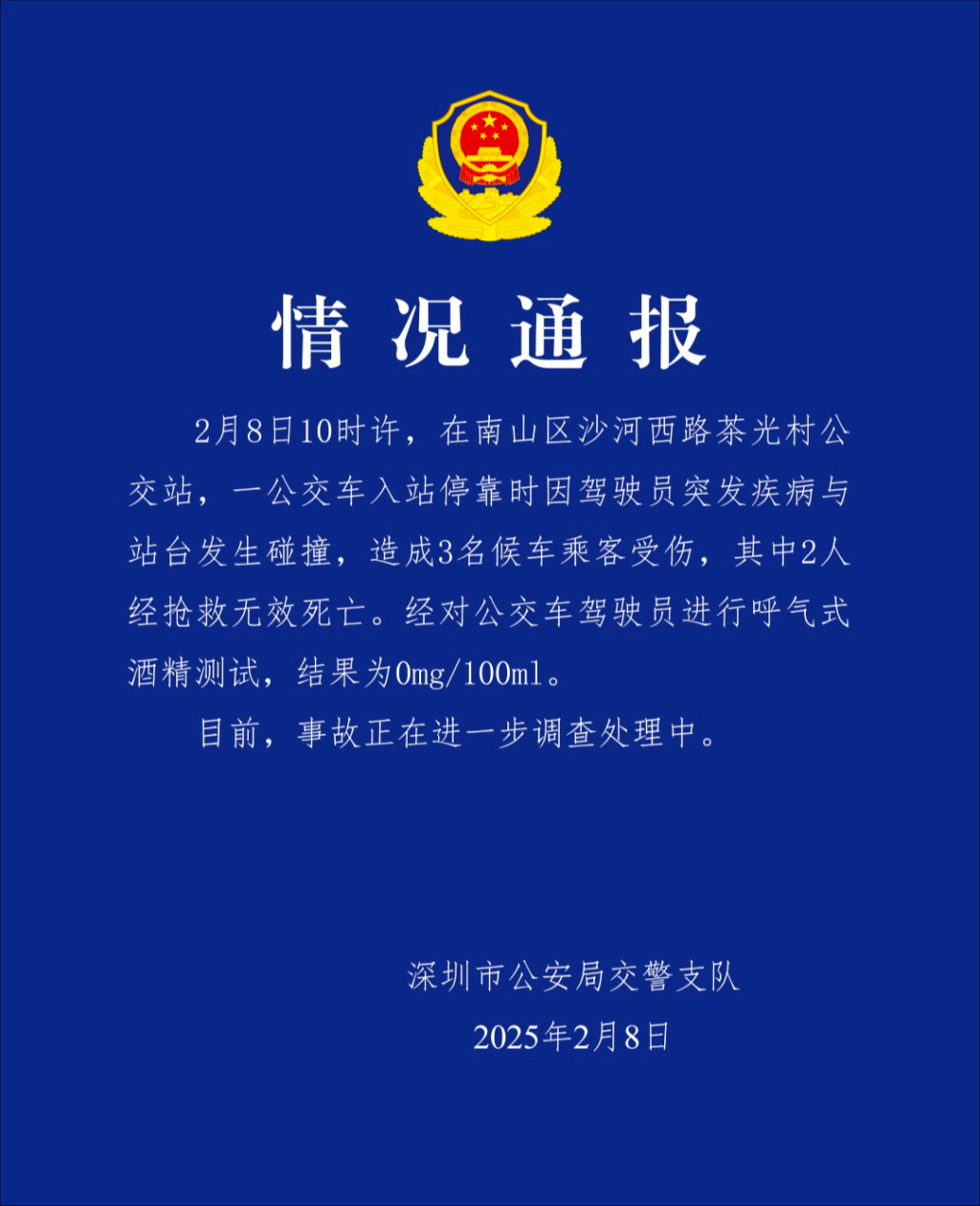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