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添加微信好友, 获取更多信息
复制微信号
《俄国思想史: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一书以欧洲思想史为镜鉴,全景式地介绍了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到20世纪初共百余年的俄国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在作者看来,俄国的18世纪和19世纪构成了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文化时代,便于人们将它视为一个结构整体。正是在这一时代,作为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在俄国出现,他们关于俄国命运、关于自身使命等问题的思考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他们围绕着传统与现代、俄国与西方、民粹与马克思主义等主要轴线的思考,呈现出俄国思想家对西方思想的接受和驳斥的过程,也有助于建构整个欧洲思想史的发展语境。本文摘自该书第十五章《两位先知作家》,澎湃新闻经译林出版社授权发布。
与出身贵族的托尔斯泰不同,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生于一个“偶合家庭”,这个家庭遭受持续的困扰,生怕失去通过巨大努力方才获得的体面的社会地位。他的天赋并非在“贵族之家”养成,而形成于一座大城市的忙乱背景之中,诸如屈辱、无法满足的抱负、每日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悲剧性的社会冲突等。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热衷的人物,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单调贫乏的人(尤见其文学处女作《穷人》),生活在其自足幻想世界中的浪漫幻想家(《白夜》),或被不健康的雄心和精神分裂症幻觉吞噬的人(尤见《双重人》)。他几乎所有小说的场景均为圣彼得堡,在一个刚刚脱离父权制情愫和感受的人看来,这座城市是一个奇异的、陌生的、不真实的世界。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圣彼得堡便很像果戈理笔下的圣彼得堡:一座雾和白夜的城市,一座脉搏不断加快的鬼城,它象征着那种源自西方、摧毁“神圣罗斯”的和平生活的力量。
如前文所述,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是被行刑队执行假死刑的囚犯之一。在宣布改判流放的最后时刻到来之前,在谢苗诺夫广场的等候是他永远无法忘怀的恐怖经历。的确,他没有理由感觉自己有罪,但毫无疑问,这种体验所造成的冲击后来诱导他十分认真地阅读《新约》中的每个字,在他于西伯利亚服苦役的四年中,《新约》是他唯一被允许持有的图书。
在鄂木斯克的苦役结束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再服五年强制兵役。他于1859年获释离开部队,重新开始写作,但他此时的思想已迥异于他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时期。1860年,他和哥哥米哈伊尔开始出版文学杂志《时代》,该杂志的主要合作者还有阿波罗·格里高利耶夫和尼古拉·斯特拉霍夫。在刊于这份杂志的文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呼吁“返回土壤”、反对激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号召回归俄罗斯人民那种“纯粹民族性的”,同时又具有真正基督教性质的价值观。
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在描绘其苦役体验的《死屋手记》一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突出强调了那些他与之朝夕相处的罪犯对他产生的关键影响。这些出身卑微、听天由命的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似乎就是普通民众的真正代表;他们虽然成了罪犯,却仍然没有放弃俄国农民那种强烈而简单的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就在那时,他敏锐地意识到了俄罗斯人民与西方化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两者之间甚至有一道深深的鸿沟;他也意识到,普通民众的价值观更为可取。
当然,其他一些因素也在他的思想演进中发挥了作用,这一演进是个复杂过程,很难面面俱到地呈现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他自己也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决定性的转折点就出现在他的西伯利亚苦役时期,正是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之间,或曰欧洲价值观和俄国价值观之间的典型对立,成为他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
186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首次出国,出色的系列特写《冬天记的夏天印象》是他对其西欧之行的描述。伦敦给他留下极深刻印象,世界工业博览会当时正在海德公园的水晶宫举行。他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力量、生活的极端理性化以及“巨大的体量”感到惊讶和震撼,这种体量不仅是外在的,而且也是“内在的,精神上的,源自灵魂的”。在博览会上,他在钦佩和恐惧之间挣扎;在他的困惑中,他觉得自己见证了某种成就和胜利,某种“终极的”东西已然发生,即“《圣经》中的某些场景,某种巴比伦场景,《启示录》中的某些预言”。帕克斯顿的水晶宫,这个巨大的玻璃和金属结构,对他而言成了资本主义进步力量的象征,尽管这是一种异教力量,一种吞噬人类的“巴尔的力量”。
在这些特写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异常敏锐地洞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分裂力量就是西方文明的动力。个人主义创造了一种强大的、具体化的物质力量,但同时也孤立了人类,使人类与自然,与他们的同胞发生冲突。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赫尔岑在伦敦相见,部分地受赫尔岑启发,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调,资产阶级自由是一种纯粹的负面品质,它本质上是“百万富翁”的自由,“能消除一切不平等”的金钱力量,与胜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构成对立,在削弱个性。这些观点最早出现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后又在小说《少年》里得到发挥。
针对欧洲资本主义的理性利己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一种理想,即东正教和俄国民间传统中留存的那种倡导真正互爱的村社理想。在这样的村社,个人并不反对集体,而是无条件地完全服从集体,不计任何得失;集体也不要求个体付出大的牺牲,却用兄弟般的友爱来保障个体的自由和安全。此类村社必须“自发地形成”,它无法被发明或被创造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观点的提出或许与斯拉夫派无关,但它们却与斯拉夫派的一些观点惊人地一致,其中就包括霍米亚科夫关于聚合性的“自由的团结”概念。
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写成一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小说描绘一个拒绝一切社会关联的人,他体现着一种抗议,反对一切服从,“对我们来说最珍贵、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个体和我们的个性”。叙述者是“一位脱离了人民准则的19世纪人”,他以其自我来反抗客观世界,抵御社会机制中的齿轮,或“钢琴的琴键,外在的自然法则在这些琴键上演奏着其喜欢的任意曲调”。他将自由解释为许可,并坚持认为,接受逻辑和常识作为通行原则,“这就不是生活,而是死亡的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位主人公挑战整个道德秩序:“是让世界毁灭呢?还是让我喝不成茶?我要说,让世界毁灭吧,为了我能永远有茶喝。”
叙述者有时会道出作者自己的想法,这个事实会使对《地下室手记》的阐释变得复杂起来。在对未来理性社会的描述中,我们再次发现了《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出现过的那座“水晶宫”:
那时……将出现新的经济关系,它们完全是现成的,同样经过数学的精确计算,于是在一刹那之间,形形色色的问题都将消失,这只是因为已然能够得出形形色色的答案。到那时,水晶宫便将建立起来……因为人是愚蠢的,极其愚蠢。也就是说,人即便完全不愚蠢,也是忘恩负义的,难以找到例外。因为,比如说,在普遍地合乎理智的未来,突然无缘无故地冒出一位什么绅士,他生着一张并不高贵的面孔,确切些说,是一张顽固落后的、嘲笑的面孔,他两手叉腰,对我们大家说道:“怎么样,先生们,我们是否来把这理智整个儿地一脚踢开,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所有这些对数表都见鬼去,让我们重新按照我们愚蠢的意志来生活?”
作者和叙述者之间的部分混淆导致了许多错误阐释,即便在今天仍有一些著作开篇就会言及,陀思妥耶夫斯基“重申了单一、独立的个体之绝对价值和完整性”。这绝非事实,因为显而易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赞成“地下室人”的个人主义,而仅同意“地下室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有的、欲将社会关系理性化的愿望所做的攻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的代表即车尔尼雪夫斯基,后者当时风头正盛)。在其《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表达一种近乎弗洛伊德式的思想,即在人类意识“黑暗的地下室”中蛰伏着种种非理性的恶魔力量,它们往往会在一个由非理性精神纽带把控的社会中得到升华,但它们很可能会奋起反抗基于“合理利己主义”的文明。由于人并非理性的存在,他们无法安居于一个理性的社会;然而,在一个缺乏真正的团结纽带的社会,“地下室人”非理性的、无政府主义的反抗便是完全合理的。在原稿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用这一论点来证明“必须信仰基督”,但令他愤慨的是,书刊审查官删去了相关段落。尽管如此,作者的意图仍相当清楚,叙述者本人也这样评论了自己的立场:
好吧,做吧。给我看一些更有吸引力的东西吧。给我另一个理想吧。给我看看更好的东西吧,我会跟着你们的。……我却害怕这样的大厦,也许因为它是水晶的,是永远不能摧毁的,也许因为甚至不能偷偷地向它吐舌头。……我自己像二乘二得四一样地知道,绝不是黑暗的地下室有多好,而完全是别的什么地方,是一种我所渴望、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地方!让地下室见鬼去吧!
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地下室人”的非理性极端个人主义的态度,与霍米亚科夫对麦克斯·施蒂纳的非理性个人主义的态度完全相同。霍米亚科夫写道,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是对理性主义文明的有效抗议:“这是一种的确不道德的灵魂发出的声音,但它之所以不道德,是因为它被剥夺了一切道德基础。这颗灵魂不断地、却无意识地重申,它渴望能够服从它希望落实并信奉的原则,它怀着愤慨和怨恨拒绝西方那些热衷于分类的人士们的日常实践。西方人自己没有信仰,却要求他人保持信仰,他们创建各种强加的关联,并期望他人顺从地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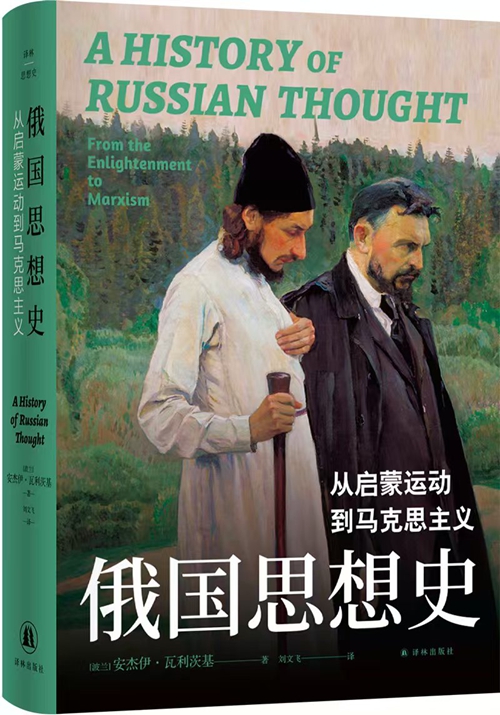
《俄国思想史: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波兰]安杰伊·瓦利茨基著,刘文飞译,译林出版社2024年11月。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