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举办“唐宋宰相与中枢体制”系列讲座正式开讲。首轮讲座由“《唐六典》对本朝宰相制度的回顾与反思”和“赵普拜相署敕问题与‘宰相’”两场子讲座组成,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张耐冬、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祎主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全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方诚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亦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陈希、苏州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丁义珏等参与讨论。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汤元宋主持。
添加微信好友, 获取更多信息
复制微信号
汤元宋首先介绍了本系列讲座的缘起与召集经历,并介绍了几位主讲人、与谈人的学术背景与研究领域。他指出,参与本场讲座的几位学者在近年内都对唐宋宰相制度相关问题有所关注,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之间相互关联、启发、商榷,对于深入了解唐宋宰相制度的各个层面都有重要意义。希望本讲座作为一个契机,推动具有不同背景、研治不同领域的学者之间相互交流与对话,从而促进学界对“宰相与中枢体制”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和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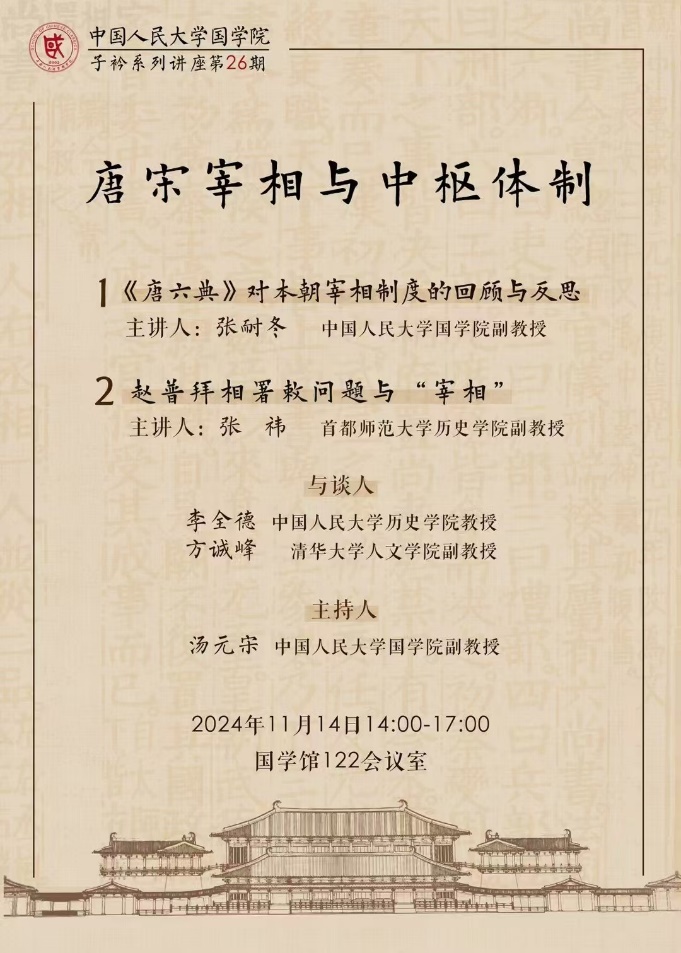
讲座海报
张耐冬以“《唐六典》对本朝宰相制度的回顾与反思”为题做第一场讲座。他从《通典·职官典》和《旧唐书·职官志》对唐代宰相的记载出发,认为在唐前期从三省长官为宰相转向高宗以后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平章事)等名号者与侍中、中书令共同任相的结构变化中,如果将侍中、中书令视为宰相结构中的“常量”,那么带“同三品”或“同平章事”的“他官执政者”则是“变量”,其变动状况与中枢政局之间存在强关联,如贞观十七年的易储与“同三品”的出现、贞观永徽之际政局对仆射退出宰相行列及“同三品”功能拓展的影响、高宗末年至玄宗即位之初的高层政治震荡与同时任相者人数激增等现象。

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张耐冬
而后,他提出应关注文献对制度的记述方式,以及其中体现出的具有时代性的内容。唐代宰相结构的变化虽在唐后期至北宋是作为共识的制度知识,但《通典》和《旧唐书》对唐前期宰相制度的概括却有明显不同。如《通典》明确提出“真宰相”的概念以描述侍中和中书令在宰相群体中的地位,这一提法源自其将“他官参掌者”与前代历史的类比,即“亦汉行丞相事之例”。杜佑认为汉代丞相具有法定的宰相资格,由此派生出其他官员“行丞相事”之例,这也是他对“真宰相”定义的出发点。而《旧唐书》则未强调“真宰相”的意义,而且认为永淳二年“同平章事”出现后,侍中、中书令与“他官执政者”“皆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种描述与《通典》的看法并不兼容,可能是较晚才出现的一种认识。因此,自近卫家熙以来将《旧唐书·职官志二》“中书令”条下此段注文视为《唐六典》卷九“中书令”条下注文的判断是不合适的。既然《通典》与《旧唐书》体现了各自所在时代(即唐中期与五代时期)对唐前期制度的看法,相比之下,编纂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唐六典》更能体现唐前期时人对本朝宰相制度的认识。

《唐六典》,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2014年再版
作为一种编写体例,《唐六典》记载某职位与宰相的对应关系时使用的均是注文,且采用的表述均为“宰相之职”,而不采用某官是“宰相”的记载方式。《唐六典》将对宰相职权的概括系于侍中、中书令这两个官职的条目之下,且描述二者的职权时并未抄录唐代《职员令》,而是采用重新归纳、自行概括的方式,突出其作为“宰相之职”的特殊权力与地位。他们所拥有的宰相权力,是掌管国家重要政务和掌枢机;体现二者地位的,则是他们作为官员领袖的超然身份。而《唐六典》在归纳前代“宰相之职”的职权时,同样突出政务处置权,说明在《唐六典》的记载体系中,宰相的职能是古今一体的。
《唐六典》在描述唐代宰相时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未记载“他官执政”的情况。事实上,对于所加宰相名号与职位严格对应的、呈现有序化特点的“他官执政者”,如尚书左右仆射,《唐六典》承认其“初亦宰相之职”,并将仆射“知国政”的时间下限定在开元时期。而对名号与职位难以建立对应关系的、相对无序的“他官执政”情况,则未予承认。张耐冬认为,从制度事实而论,开元时期同时入相的人数减少,曾经无序的任相行为也似乎在恢复正常,玄宗亦尝试对宰相结构进行制度上的调整,如令左右仆射兼侍中、中书令;在观念层面,开元时代的人们在反思前几十年间政治的氛围下,可能不再将“他官执政”看作曾经的制度常态,反而认为那只是历史上偶然出现的政治乱象。因而《唐六典》反映了这种对制度的认识,并坚持认为宰相制度需有规则,即宰相的身份和地位必须与具体官职严格对应。这并非《唐六典》编者的个别意见,而是一种思潮。在唐朝建国百年之际、玄宗意欲总结本朝典制以垂范后世的背景下,时人对宰相权力、地位与宰相制度有所思考,并形成共识,这种共识集中体现在《唐六典》的相关文字中。玄宗与张九龄就封赏牛仙客之事发生争论时,张九龄“陛下使臣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合尽言”的言论,体现了他对宰相职权的认识,其观点与《唐六典》对宰相职能的归纳相契合,也可作为一个例证。
张祎以“赵普拜相署敕问题与‘宰相’”为题做第二场讲座。他从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对赵普拜相署敕之事的评述引入话题,并有所辨正。
钱穆对此事的概括是:“建(乾)德二年,恰逢三个宰相相继去职,太祖欲派赵普为宰相,但皇帝诏敕一定要经宰相副署,此刻旧宰相既已全体去职,一时找不到副署人,该项敕旨,即无法行下。……宋太祖乃召集群臣会商办法,当时有人献议说:‘唐代皇帝曾有一次下敕未经宰相副署,此在甘露事变时,当时前宰相已死,皇帝临时封派宰相,即由尚书仆射参知政事者盖印,今可仿此方式办理。’同时即有人反对……如是再四商讨,始决定由当时开封府尹副署盖印行下。”由此,钱穆以此论述中国古代政治“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的专制”,“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张祎指出,钱穆对此事的理解存在偏差,而且似乎过度拔高了该事件的意义。

主讲人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张祎
张祎结合北宋时代任相流程以及文书运作的机制,认为赵普拜相署敕事体现出的更多是宋代文书行政中的制度流程问题,而非君臣权力制约问题。赵普拜相一事涉及多种行政文书的运行,从《宋会要辑稿》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到三种与此事有关的行政文书:制书、告身、敕牒。其中,对于宰相等重要官员的任命来说,最重要的步骤是制书的起草与宣读,因为皇帝颁下的制书是唯一能决定宰相任免与否的文书;而后续的告身和敕牒则是官员上任时的身份证明,“受告敕”只是走程序,不影响任命的有效性。进行到“署敕”这一环节时,任命的决定其实早已完成,而且在制书颁下之时已经生效,只有一些后续手续需要补全。有时甚至可以从存世文书中见到受任命者本人的签名,《司马光拜相告身》和《范纯仁拜相告身》中都可见到司马光、范纯仁本人的签名。二人在自己的拜相告身上签名,是遵守宰相要在告身上署名的规定,也就是说,在二人签字的时刻,即拜相告身尚未生效下发的时刻,他们已经在以宰相的身份办公了。这也说明宰相任命与身份的生效与否并不由告身和敕牒决定。

《宋人书司马光拜左仆射告身》(局部)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进宫与宋太祖商议赵普拜相的署敕问题者,正是赵普本人。面对这一程序性问题,宋太祖提出的处理方式是“卿但进敕,朕为卿署字,可乎?”赵普则回答称“此有司所行,非帝王事也”,认为署敕问题属于行政流程与制度问题,皇帝干预则有失体统。于是宋太祖召翰林学士入宫商议此事,并最终采纳了窦仪有关“今皇弟开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的建议,即由时任开封府尹的赵光义来签字。赵光义有“使相”的身份,带同平章事衔,名义上也有宰相的身份。窦仪的这一提议极为切实可行。唐后期即开始出现使相在敕牒上列衔(但并不真正签字)的例子,至北宋时,使相挂名事虽已大大减少,但在少数敕牒(如任命宰相的敕牒)中仍有保留。因此,由赵光义来签署赵普拜相的敕牒,操作起来非常方便。
综上可见,赵普拜相署敕一事更多关乎官员任命后的文书运行程序问题,而较少反映出宰相对皇权的制约。钱穆选择这段材料来论证中国古代的“开明专制”,因为对宰相制度抱有较高的期待,从而造成过度解读。
两场讲座的共同特色,是主讲者在所讲个案分析或文献解读的基础上,都对“宰相”概念或“宰相制度”的定义做出反思。
张祎在解析赵普拜相署敕事的意义后,转向了对“宰相”概念本身及其体现出的政治理念问题的探讨。他指出,“宰相”概念是中国古代“委任责成”政治理念的体现。所谓“委任责成”,即君主将国家政事委托给“贤人”或其信任的官员来进行处理,自己则不直接介入具体事务,只对官员的表现进行评判和奖惩的皇权行使模式。《荀子·王霸篇》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都有体现“委任责成”观念的内容。传统的讨论往往倾向于以理想状态下“委任责成”的执政方式来认识现实的政治体制,并以此作为辨别某个官职或某个机构属于宰相、宰相机构的依据。但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中,实际的官僚体制设计却往往并非基于纯粹政治理念的引导,而是分科分层应付政务的实际需要。所以,现实的职官架构中经常很难说清哪些官员属于真正的“宰相”,莫衷一是。这是因为“宰相”实际上是基于传统政治理念的一个分析概念,而非古代官僚体制一贯实有的事物。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批评明代废除宰相制造成“无善治”的后果,并认为明代内阁并非真正的宰相,这一论述对后世的学术讨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祝总斌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中提出宰相需具有议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两项职权,二者缺一不可,正是对此议题的回应。经过祝先生的阐发,足以透彻解释明清内阁、军机处与前代“宰相”制度之间的根本差别所在,“宰相”这一分析概念的重要价值已然得到妥当、充分的开掘了。
离开长时段的宏观把握,具体到宋代的中枢制度,就会出现“宰相”分析概念与“宰相”史料记载的扞格、窒碍问题。宋代中枢为两府制,负责民政的中书门下(元丰以后为三省)和负责军政的枢密院两个机构地位最为重要,根据祝先生的定义,都应该属于宰相机构。但这两个机构的官员在宋代史料中大多并不能称为“宰相”。宋代称呼两府官员为“宰执”或“宰辅”,分为“宰相”与“执政”两个群体。“宰相”特指北宋前期中书门下或元丰改制后三省中的正职官员;两府中其余的官员则被称之为“执政”,包括中书门下或三省的副职官员(参知政事、左右丞、门下侍郎等),也包括枢密院的正副长官。宋人对于“宰相”所指对象的这种特殊强调,可能与这一时期的士大夫政治理念有关,属于“委任责成”思想的一种投射或反映。但这样一来,沿用祝总斌先生的论述,就不可避免出现学术概念与史料记载之间的矛盾与“别扭”:在宋代,那些根据他的定义应该被视为“宰相”的官职和机构,时人却不目之以“宰相”;在明清两代,经常被人称为“相公”“相国”等的内阁、军机处大臣,却又不能在他的定义下视作“宰相”。究其原因,是因为祝先生所界定的“宰相”概念只是传统时代政治理念下的一个概念。祝先生的阐释能够很好地回应黄宗羲的论断,但在面对一些具体史料和称呼习惯时,却仍要陷入歧互扞格的困境之中。因此,今天的制度史研究要继续推进,应该扬弃作为分析、定性概念的“宰相”,学习祝先生的思路和方法,转而发展、界定诸如“决策权”、“政务官”、“行政机构”之类的概念,以便将来可以把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地区的所有政治体都放在统一的概念体系下进行精密的讨论和分析。
张耐冬也对唐代宰相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有所反思:在唐前期“他官执政”现象大量出现的情况下,对“宰相”和“宰相制度”的界定是否还能遵循《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的思路?祝总斌先生认为两汉的三公、魏晋南北朝的尚书台(省)长官是宰相,这与《唐六典》对宰相的认识相一致,即宰相职权与地位应和具体职官相对应;但唐代大量出现带“同三品”“同平章事”等名号任相者,他们不具有职位与宰相身份对应的可能,而若采用《旧唐书》的说法,将“同平章事”等名衔作为宰相的固定对应物,恐怕不能保证带此类名号者同时拥有宰相的权力和地位。换言之,考察唐代宰相时,是否能像研究汉魏南北朝宰相一样,认为该时期存在相对稳定的“宰相制度”,或者说,应如何定义“唐代宰相制度”?由此话题,他进一步引申到对学界概括唐代宰相制度时曾使用的若干说法的反思,如“宰相制度的使职化”,以及“差遣制宰相”“员外宰相”“兼职宰相”等概念。这些说法都是基于《通典》《旧唐书》等文献的记载,这些文献在描述唐代制度事实的同时,对制度的理解带有极强的时代感;但这些时代意见往往被研究者未加甄别地接受。如何处理才能不被其中某一种时代意见所囿,仍是值得反思的问题。此外,《唐六典》《通典》《旧唐书·职官志》等各种史料内部也存在描述方式与内在逻辑的不同,理清这些史料的表述逻辑,才能更好地辨析其中的事实记录和时代意见。

讲座现场
随后,与会学者围绕“宰相”概念、宰相和中枢体制的关系、不同时期的宰相在中枢政治中的作用、两场讲座使用的重要文献等几个主题展开讨论。其中,有关“‘宰相’概念”和“不同时期宰相在中枢政治中的作用”两个话题是与会学者的讨论焦点。
陈希从蒙元宰相制度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出发,探讨其与唐宋宰相制度之间的联系、互动与影响。她指出,形成于窝阔台统治时期的大蒙古国行政体系中,出现了包括“大断事官”与“重臣必阇赤”在内的“宰相”群体。其中,大断事官可以被视作大蒙古国时期宰相制度中的“常量”,其地位很高,可以介入黄金家族内部的纠纷和事务。而据波斯文材料,必阇赤的长官被称为“大必阇赤”,耶律楚材等处理政事的官员可以被称为“重臣必阇赤”,这批官员更类似于中原王朝的宰相群体。在大蒙古国的宰相制度建构中,游牧民族内部原有的主奴观念发挥着很大作用,这与唐宋等中原王朝有所差别;不过,唐宋以来(具体而言,大蒙古国直接接触到的是金)的官制与君臣关系也对大蒙古国内部的政治理念产生了影响,“重臣必阇赤”群体地位的上升和职权的扩大即源于此,从大蒙古国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这一变化可视为一种进步。
丁义珏从知识史的视角出发,认为人们在认识自己所在时代的制度时,往往要借用前代的概念,宰相这一概念就是在历代不断借用、套嵌前代制度史知识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在讨论宰相相关问题时,不能完全从职事和行政程序的角度上来考察,而需要重视宰相拥有特定身份的问题。赵普拜相署敕事在当时引发的讨论和在文献中留下的记载,恰恰说明时人对官员任命程序合法性和“宰相身份”问题的重视。
方诚峰对“宰相”的概念和相关经典研究发表了看法。他认为宰相是“枢机”的一种,而掌握“枢机”之权者不限于宰相;同样,“委任责成”确为宰相职能的重要部分,但并不等同于传统认识中宰相的全部意涵,更不能仅从“委任责成”的角度来理解宰相。他指出,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对“宰相”的界定与作者的法学背景、从现代行政制度特别是行政效率的角度解释古代制度的思路有关,该书也明确反对从君相矛盾的角度解释宰相制度的演变,在以上背景下对“宰相”作出的定义,无法解释元明清历史语境下的“宰相”。
有关“宰相和中枢体制的关系”,学者们也做了深入探讨。张亦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一是赵普拜相署敕事件中,所谓与“皇帝”对举的“有司”应当如何理解?二是如何看待君主、宰相和有司等概念与“朝廷”之间的关系?三是宋代中书门下和枢密院的宰相机构地位如何发育而来,与其“掌枢密”的职能有怎样的联系?他认为,这些概念仍有再思考和讨论的空间。李全德提出,有关唐代宰相“知政事”的说法,与各种文献中将侍中、中书令视为宰相的观念似乎有出入。与“知政事”最为符合的机构和官员应是尚书省及其长官尚书左右仆射,但仆射在唐代却失去宰相地位,反而是侍中、中书令保有宰相身份,这与中书、门下两省掌“枢密”“机密”的职能有何关联?陈希则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讨论元代尚书省的职权与地位,她认为,对元代君主而言,尚书省最大的功能是理财,这与中原政权的尚书省区别很大。历史上曾经历过突厥化的波斯地区也强调财政的重要性,例如波斯最高执政官大维齐尔最重要的职权就是财政权。可能对于游牧民族政权来说,行政事务的实际管理重点就在于财政。

《阿拔斯一世与瓦利·穆罕默德汗》,伊朗伊斯法罕四十柱宫壁画(局部)
对“讲座中使用的重要文献”的讨论,集中于对《唐六典》文本性质的讨论。李全德认为,《旧唐书》“中书令”条注文不一定与《唐六典》完全无关,而可能是参考《唐六典》后自行作出了文字的改动,因为《旧唐书·职官志二》中有大量内容与《唐六典》一致,可以视为对后者的摘编。方诚峰认为,目前对宰相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官职与宰相的对应关系上,而这种对应关系在历史上只存在于中书门下体制建立之前。《唐六典》的成书虽然在中书门下体制建立之后,但本身存在着一种复古倾向,与制度实际不完全吻合。这提示我们在对《唐六典》中提及的官职执掌和相关概念作分析时,需要辨别其究竟是对当时制度的写实,还是基于某种政治理想所作出的再写作。张亦冰提出,《唐六典》的体例决定了其在面对新制度时无法另起炉灶进行讲述,但其仍然力求在不打破令式框架的前提下,通过正文和注文之间的叙事互动,体现出制度的演进和变化,充分呈现开元时期制度的新变化。



清华大学副教授方诚峰、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张亦冰、中国人民大学讲师陈希等学者发言
在场听众还就唐宋宰相权力与秦汉宰相权力的关系、能否界定明清内阁为“宰相机构”、军机处与唐宋宰相的本质区别等问题进行了提问,两位主讲人和在场学者也就这些话题做了回答和延伸讨论。参与讨论的学者都表示,学界对于“唐宋宰相与中枢政局”的讨论,应在今后以讲座、读书班、工作坊等形式持续深入开展,以期待对这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能进一步碰撞思路、凝聚议题、提升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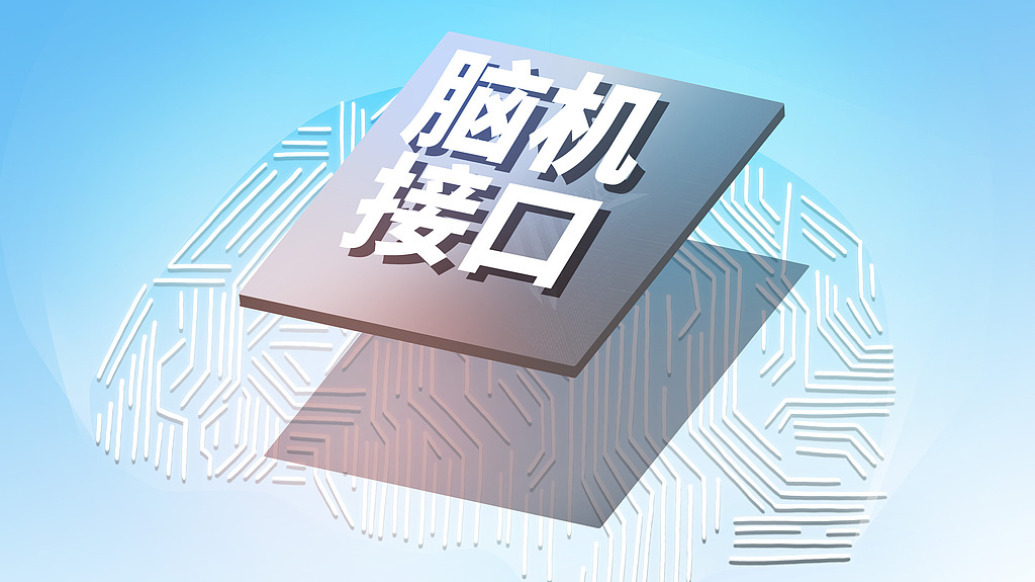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