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曾回忆说,他所写的《袁崇焕评传》发表后,史学家向达曾去信指正。事实上,这件事情迂曲乖谬、古怪离奇,非但向达未曾参与其中,金庸也始终蒙在鼓里。对这段学林往事予以考索,可增趣识。
添加微信好友, 获取更多信息
复制微信号

向达
金庸的小说都曾在报纸和杂志上连载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开始全面修订自己的小说,定名为《金庸作品集》陆续出版,其中《碧血剑》一书后面附录的《袁崇焕评传》是金庸所写的一部人物评传,袁传在叙事与评议时情感丰沛,着意渲染、还原明末清初朝代更迭时的历史气氛,其著述体例更像一篇史论,而不像一部专著。
金庸在《碧血剑》第二和第三版后记里对《袁崇焕评传》的说法有出入,略引两版后记相关说法如下:
一、《碧血剑》第二版后记写于1975年,金庸在文中说,“《碧血剑》是我的第二部小说,作于一九五六年”,袁崇焕和金蛇郎君这两个“在书中没有正式出场的人物”才是小说真正的主角,由于小说明面上的主角袁承志性格不够鲜明,“袁崇焕也没有写好,所以在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间又写了一篇《袁崇焕评传》作为补充”,“现在的面目,比之在《明报》上所发表的初稿《广东英雄袁蛮子》,文字上要顺畅了些”(金庸《碧血剑》,三联书店1999年版,687页)。

《碧血剑》,三联书店1999年版
二、《碧血剑》第三版后记写于2002年,金庸在文中不再说《袁崇焕评传》写于“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间”,改说“书末所附的《袁崇焕评传》,写作时间稍迟”,并提到“《袁崇焕评传》一文发表后,得史家指教甚多,甚感,大史家向达先生曾来函赐以教言,颇引以为荣,已据以改正”(金庸《碧血剑》,广州出版社2013年版,785-787页)。

《碧血剑》,广州出版社2013年版
《袁崇焕评传》1975年5月23日开始在《明报》连载,同年6月28日连载结束,完整标题为《广东英雄袁蛮子——袁崇焕评传》,金庸在连载第一期的题记里写道:“为了修订改写武侠小说《碧血剑》,近几个月来读了一些与袁崇焕有关的资料……因此我试写了这一篇文字。其实这不能说是‘评传’,只是一篇‘读史感想’。这篇文字本有许多条附注,说明资料的出处,相信报纸的读者不会感到兴趣,所以在这里都略去了。这些注解与有关图片,将来发表在《碧血剑》的修订本里。”(连载第一期的书影见严晓星《金庸年谱简编》,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290-291页;另见邝启东《另类金庸:武侠以外的笔耕人生》,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23年版,109页)同年10月,《碧血剑》修订版(即第二版)的上下册出齐。
向达1966年11月24日在北京去世,时年六十六岁。向达逝世的时间并无疑问,二十年后向达的学生陈玉龙有回忆文章发表在《人民政协报》上(见沙知编《向达学记》,三联书店2010年版,37-41页),陆键东见过官方内部材料《向达生平档案》,也曾在书中述及(见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419页)。从《袁崇焕评传》连载第一期起首的题记来看,初稿发表于1975年这点也没有疑问。矛盾的地方在于,向达已在1966年去世,怎么可能看到1975年才发表的《袁崇焕评传》?
据媒体报道,2022年中国大陆首次举办“金庸展”,其中部分展品系首次展出。经湖北省图书馆工作人员提示,咨询该展览的主办单位香港特区政府驻武汉办事处,得知与信札相关的展品只有一件“查良镛致《明报》编辑部手谕”。不过在香港文化博物馆的藏品中倒可以拎出一条线索,该馆藏有金庸使用过的资料簿(编号HM2020.11.109),一共三十一份,由金庸家人捐赠,标签均由金庸手书,其中有一份标注为“学者函件”,但经馆方郭义浩先生检视,答复未能找到与向达相关的信札。
不过,基础文献的缺乏,并不妨碍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向达去世在前,金庸《袁崇焕评传》的初稿发表在后,这两处相互矛盾的事实无论如何翻不过去,向达从未写信跟金庸谈论《袁崇焕评传》,这一点是确凿的。
在《碧血剑》第三版后记中,金庸把关于《袁崇焕评传》写作时间的话挪到前头,开篇就说:“《碧血剑》是我的第二部小说,作于一九五六年。书末所附的《袁崇焕评传》,写作时间稍迟。”从明确的“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间”,变成模糊的“写作时间稍迟”,不能说明金庸已经发现向达的去世时间和《袁崇焕评传》的写作时间对不上,因为那样的话金庸只需要重新核对那封信的署款日期,就必然会发现那封信是1975年《袁崇焕评传》在《明报》连载之后才寄达的,金庸自然不会把这件事说出来。何况第三版后记相对于第二版,除了在内容和表述上做了调整(如修改《碧血剑》的增订篇幅比例,模糊《袁崇焕评传》的写作时间),也删掉了一些话(如小说的真正主角是袁崇焕和金蛇郎君,小说明面上的主角袁承志性格不够鲜明等),还添加了很多与本文讨论的问题无关的话,“写作时间稍迟”只是纯粹的文字细节调整而已。金庸过世后,广州出版社又出了一套金庸作品集的“典藏本”,该版《碧血剑》的后记跟第二版没有不同(金庸《碧血剑》,广州出版社2020年版,779页),所谓的“典藏本”其实就是第二版,就材料而言并不新异。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金庸当年收到那封信时,并不知道向达已于1966年去世,时间久了更不会意识到有问题,2002年在《碧血剑》第三版后记中提到向达,以至后来新修版(即第三版)多次再版重印,金庸仍不知道向达是1966年去世的,而是以为向达至少是在1975年寄出那封信之后才去世的,向达逝世的时间本就是个相对冷僻的知识点,不知道很正常。
金庸说《袁崇焕评传》发表后“大史家向达先生曾来函赐以教言,颇引以为荣,已据以改正”,表述是很明确的。要说金庸将他人来信误记为向达,也不是没有可能,但金庸1996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自己一年前因心脏病做过一次大手术,“新闻工作已经做到没有精力再做了,小说家也差不多了……最大愿望就是,还有几年这个生命的话,这个有限的生命主要拿来研究学问”。“向达”的指教对金庸来说显然是有分量的,应该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若把错误归给记忆的话,未免过于简单粗暴了。
不妨提出一种假设:问题也许出在那封信上,有人冒用向达之名写信给金庸!
循着这一假设往下走。冒名写信的人,动机究竟何在?不妨来看两个类似的例子。其一,1934年有人冒名汪静之,在《春风周刊》上撰文骂《读书顾问》主编王平陵,汪静之发现后写信向王平陵解释,《春风周刊》的编辑之一孙望是汪静之的学生,却连他也没能在事前发现端倪(见金传胜《“关于冒名骂人”:汪静之致王平陵的一封集外书简》,《名作欣赏》2023年第19期)。其二,1964年一位从事税务工作的青年毛国瑶写信给俞平伯,说他认识的一位叫靖应鹍的人家里收藏有一部前所未见的《红楼梦》抄本,该抄本后来遗失了,但他此前已经把其中一百多条脂批抄录下来。由于这些批语涉及脂砚斋、畸笏叟是不是同一个人,曹雪芹去世的年份,小说八十回后佚稿的部分内容等重要问题,由此引出《红楼梦》研究的诸多讨论与争议,至今仍存在重大意见分歧。而红学界一直存在一种观点,认为由毛国瑶辑录的靖藏本批语是伪造的(见高树伟《毛国瑶辑“靖藏本〈石头记〉”批语辨伪》,《文史》2022年第4期)。这两例背后的动机,或许有利益的驱使,也有可能是出于戏弄他人以取乐的心态。
假如金庸遇到的情况也类似,那么几件事的区别仅在于,冒用向达之名写信给金庸的人至少提出了有用的意见,当然,那应该只是报刊上时而出现的“本刊更正”之类的意见,没想到骗了金庸几十年。
也许只有这样迂回的假设才可以跟这件事情的古怪相匹配,但材料上别无可据,就跟径直将错误归因于误记一样,令人不满又无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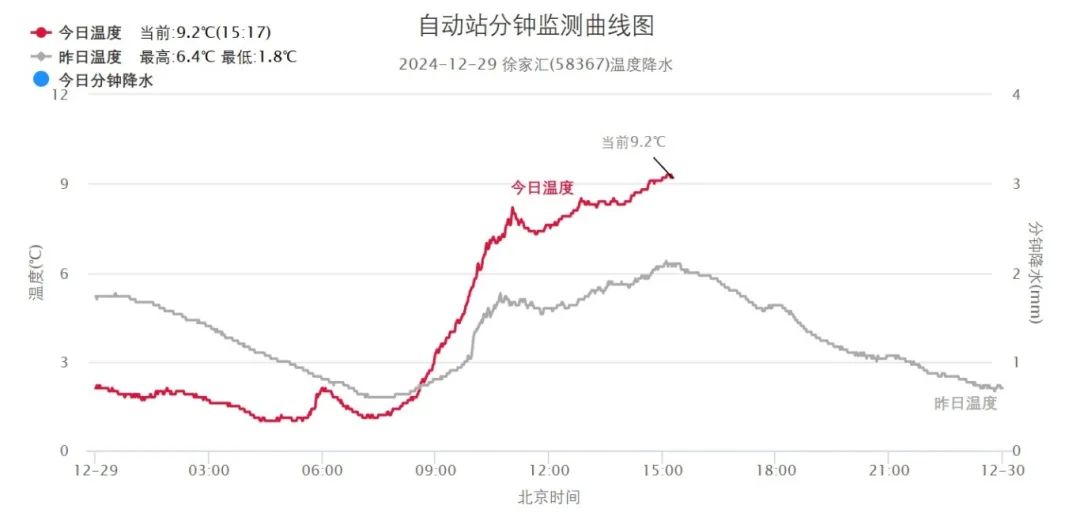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