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是民族历史书写的舞台。它不处于十字路口,只是一个岛屿,远离欧洲其他地区,也远离欧洲历史的大部分事件。在历史学家和古文物研究者看来,爱尔兰的边缘性是习以为常的现象。这些研究者倾向于附和并不断重复以下事实:爱尔兰从来不是罗马帝国的组成部分。对于如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这样的历史学家而言,此事则是一种耻辱,因为欧洲的所有地区正是从罗马获得其礼仪规范的。对于民族主义者、19世纪的作家们而言,这却是值得自豪的一点——爱尔兰仍然保持着它原初且本土的真实性:“爱尔兰让大陆民众垂涎已久……然而只有罗马人才差点去征服爱尔兰。”这一观点可追溯到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莱布尼茨在其《词源汇总》(Collectanea etymologica)里便推测过欧洲语言与(特别是)凯尔特语言之间当时还未明晰的关系。他指出,爱尔兰的边缘性让该国及其语言变得有趣,因为它未曾受到稍后移民浪潮的影响,而后者曾搅乱了欧洲的种族-语言版图。爱尔兰的语言或许得以安全保存下来,因此变得更古老、更原始,特别是同(例如)威尔士语相比。(在凯尔特文献学家之中,这一观点仍占据主导地位。)
添加微信好友, 获取更多信息
复制微信号
爱尔兰的民族历史学家发现,他们很难如同日耳曼类型那样,从原始种族真实性的角度来分析爱尔兰历史。尽管他们清晰地沿循如下叙述路线:即证明该国的盖尔人(Gaelic people)才是原初居住者,且受到英格兰王室及英裔爱尔兰人殖民阶层的非法镇压和剥夺——但当地传统本身却远远没有把盖尔凯尔特人视作本国土生土长的居民。

爱尔兰圣科尔曼大教堂
当地伪历史神话学业已把爱尔兰视作一个不断被前后相继的移民浪潮所占领的国家。中世纪错综复杂的“起点”神话与吟游诗人的故事甚至还带有如“占领爱尔兰之书”(the book of the takings of Ireland)这样的题目。根据该观点,盖尔人只是一系列征服者中的最后一群人,在此之前还有费尔伯格人(Fir Bolg)、达努神族(Tuatha Dé Danann)及其他种族。这种观点被17和18世纪印刷出版的近代历史书写作品所继承,特别是通过杰弗里·基廷(Geoffrey Keating,约1569-约1644)的著作(拉丁文,17世纪20年代)。在这种观点下,爱尔兰是一块在那儿“等待被占领”的土地。正如一位中世纪吟游诗人表达的那样,它是“刀剑之地”,不是用法律或封建头衔来占有,而是用统治者的军事力量、文化馈赠与个人魅力来加以控制的。英格兰或亲英的历史学家拒绝接受本土传统,将之视作愚昧土著人的迷信神话,而且把12世纪晚期英格兰王室军事入侵前的所有爱尔兰历史之地位降低为传说中的史前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论点毋宁说是一种教会历史的论点:即关注这个国家在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化是否是在教皇权威的基础上进行的。有关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的主教地位是否低于罗马主教的问题,正是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分属天主教会、高教会圣公会、长老会的作家们各自阐述的焦点。
于是,19世纪爱尔兰的民族历史书写面临着一种尴尬的三重困境。首先,它不能再天真地重复中世纪传说般的伪史学,而必须向17和18世纪期间在历史书写方面取得的明显进步妥协,如由马比昂(Mabillon,1632-1707)和穆拉托里(Muratori,1672-1750)带来的史料考证与史料编辑,由伯内特(Burnet,1643-1715)、克拉伦登(Clarendon,1609-1674)和休谟带来的“哲学化”历史写作之发展。然而,另一方面,他们虽同情盖尔人的传统,但这些传统却被现代历史书写视作空想与幻想而遭到摒弃。尽管如此,即使在该传统的观点下,爱尔兰盖尔人也仅仅是前后相继的各族群链条中的一环。它的前面有费尔伯格人和达努神族,而它自己则被丹麦人和英格兰人所取代。那么,如何解开这一棘手难题呢?
答案伴随着印欧语范式的发明而来。在1780年至1825年间,比较语言学确定,爱尔兰的盖尔语构成了凯尔特语族的一部分。此前的爱尔兰古文物研究者和历史学家都把盖尔人——当时广泛被称为“米利都人”(Milesian),即米勒人(Míl)的后代——视作有源头可循的民族。他们可被追溯到腓尼基人(Phoenician)、迦太基人(Carthaginian)和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这些族群通过西班牙的陆路与大西洋沿岸的航线,从地中海到达爱尔兰。东方主义视角遭到抛弃,随之而来的激烈历史争论和考古争论占据了19世纪20-30年代的主流。其焦点是一种印欧模式,即把盖尔凯尔特人视作大陆高卢人与不列颠人(Briton)的同族人,而高卢人与不列颠人早在铁器时代之初便从欧洲内地到达爱尔兰。由此,盖尔人“征服”(Landnahme)爱尔兰之举,便成为在历史学和考古学上得以确立的全欧洲范式的组成部分,并巩固了爱尔兰盖尔人的主张。后者认为,他们曾是该国最古老的历史族群之后代,是本地的,土生土长的,并且这是得到证实的。此举把盖尔人之前的费尔伯格人和达努神族等压缩到未知的、已消失的、“史前”巨石建造者和神话人物的阴影之中,同时把夺取权力的丹麦人和英格兰人转变为入侵的掠夺者、占领者和殖民者。因此,P. W. 乔伊斯(P. W. Joyce,1827-1914)在其《古代爱尔兰社会史》(A Social History of Ancient Ireland)中便这样写道:
古代爱尔兰的制度、艺术和风俗,除却少数例外,都是在几乎完全不受外来影响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罗马人从未踏足爱尔兰;虽然他们的影响在某些细微层面上能被人感受到,这些影响或是通过直接交流,或是间接通过不列颠人产生。第一批以侵略者身份出现的外国人是丹麦人,……然后是盎格鲁-诺曼人……。但是,丹麦人和盎格鲁诺曼人入侵的一个重要影响必须在此指出:他们阻止了当地学问与艺术的进步……爱尔兰展现出一个被阻止发展之文明的奇景。
我们或许可以放心地把托马斯·穆尔(Thomas Moore,1779-1852)的《爱尔兰史》(History of Ireland,4卷本,1835-1845年)称作该国19世纪第一部主要的、充满雄心壮志的民族史。该书的第一卷出版于1835年。作者作为拜伦(Byron,1788-1824)的朋友及后者的传记作家、文集编辑而闻名于世。此外,他还是这一代人中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作为诗人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伟大诗作《拉拉鲁克》(Lalla Rookh)及其爱国主义的《爱尔兰旋律》(Irish Melodies)。当穆尔接受撰写一部“爱尔兰史”的任务时,历史书写正好从其激烈争议(包括世俗与教会的)、好古主义与“纯文学”(belles lettres)的史料传统中产生。随着1798年起义与1800年至1801年《联合法案》(Act of Union)的余波和相互指责逐渐退入过去,世俗性争议正在减少。1829年《解放法案》(Emancipation Act)让爱尔兰占多数的天主教人口获得公民权利后,宗教争议逐渐减少。穆尔参加了上述两场争论,并由此写下了他的《洛克上尉回忆录》(Memoirs of Captain Rock,1824年)和《一位爱尔兰绅士寻找信仰的旅行》(Travels of the Irish Gentleman to Search of Religion,1833年)。好古主义正在慢慢褪去它那矫揉造作的业余作风与毫无顾忌的东方主义式猜测,并开始依仗来自本土史料的数据进行更深入的认识。这些本土史料已开始由查尔斯·奥康纳(Charles O’Conor,1764-1828)与爱德华·奥赖利(Edward O’Reilly,1765-1830)等学者进行整理。最后一批支持东方主义学派“腓尼基缘起论”空想者,例如威廉·贝瑟姆爵士(Sir William Betham,1779-1853)正日益被边缘化,并遭到嘲笑。因此,穆尔的史书便颇为自信地以一段关于“爱尔兰的凯尔特起源”之段落展开。

托马斯·穆尔
然而,穆尔发现自己很难完全摒弃那些来自传说性的、伪历史的本地传统中的原始材料,无论它们是否站得住脚。复述早期神话中的征服历史实在是根深蒂固的观念,而且当时也不存在其他可用信息。其结果是,穆尔及在他之后的绝大多数19世纪历史学家,都选择了一种黑格尔式的“扬弃”(Aufhebung):在其文本中,他通过对传说的神话本质加以批判性描述,将这些不可信的传说载入其文本;而后他以一种调查开始自己的历史叙述——这种调查并不针对这片土地及生活其间的部落,而是针对古代史料及其内容。由此,历史叙述便几乎无缝地从一种针对神话与史料的考证序曲中孕育而生。
由此,这就是“开启”一段爱尔兰历史的可被接受之方法。开头几章描述与解释了一连串从远古时代以来流传的神话与传说,而没有在事实上认可它们。在这种描写技巧后,文本开始转向描述生产那些神话与传统的土地和社会。这是爱尔兰人口地层的首个真正的“历史”岩层:盖尔人。然后,历史继续向前发展,通常由圣帕特里克的基督教传教开启。由此,盖尔人的爱尔兰被凸显为该国真实最主要的身份认同之代表,即便这一点并不能为历史叙述布置一个显而易见的开场或场景设置。
这段叙述的结尾用上了一种对偶技巧。在史书以悲剧英雄的形式追溯了盖尔人被入侵的英格兰军队所驱逐,以及他们注定失败但从未放弃对邻国霸权优势力量的抵抗后,这段叙述的结尾拒绝把自己呈现为这段发展的谢幕。爱尔兰史总是延续到当下,并以一个或多或少明确的呼吁而结束,以便不让问题仅止于此:未来必须朝着夺回爱尔兰真正的身份认同与独立的金色理想前进。于是,如同这段叙述的开端并非爱尔兰真正历史的开端那样,这条故事线的结尾同样不是故事的落幕。
爱尔兰历史这种激进的开端-结尾模式,同样反映在它们强烈导向互文性的循环与更新的倾向之中。这一点本身就值得强调。正如安·里格尼所指出的那样,历史书写不像小说写作,其特征在于一种“竞争性趋向”。历史学家一遍遍地回到此前已被研究过的时间段,因为他们感到其先行者并未完全而令人满意地完成这项研究任务。所有历史学家都以其先行者的不足来证明他们回到既有话题的正当性,如他们引证最新发现的档案材料,或纠正他们感到被曲解、不完整或不充分的解释。历史学家之间的互文性自然而然是竞争性的。W. E. H. 莱基(W. E. H. Lecky,1838-1903)纠正J. A. 弗鲁德(J. A. Froude,1818-1894)的盎格鲁中心论之举,便是爱尔兰学术历史追随前文模式的一种例证。但是,爱尔兰的公共叙述性历史书写,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其本质不仅仅是偏颇或好辩,而是在其修正更古老观点时明显表现出非竞争性面貌。面对先行者,它采取了消化吸收而非拒斥的态度。18世纪的研究者,如西尔维斯特·奥哈洛兰(Sylvester O’Halloran,1728-1807)或詹姆斯·麦盖根(James MacGeoghegan,1702-1763)都让自己追随基廷及《征服爱尔兰之书》的传统,随后他们自己又被19世纪的后来者所吸收与重复。他们的著作得到重印,并由现代的民族主义研究者所延续,如A. M. 沙利文(A. M. Sullivan,1829-1884)和约翰·米歇尔(John Mitchel,1815-1875)。因此,在1865-1868年间,出现了下列现象:由阿贝·麦盖根(abbé MacGeoghegan)……从最可信的史料中编撰爱尔兰历史(古代与现代);从《利默里克和约》(Treaty of Limerick)直至当下的延续性,由约翰·米歇尔(John Mitchel)完成——这种前进中没有明显的中断,从中世纪的“起点”之谜直到当代分离主义政治。同样,在1884年,出现了一本以类似方式组织起来的多卷本著作,题为“爱尔兰图史,从米利都人登陆到当下”(The pictorial history of Ireland, from the landing of the Milesians to the present time)。它正好与西尔维斯特·奥哈洛兰的18世纪史与A. M. 奥沙利文的19世纪史结合在一起。它的副标题几乎包含了内容概要,再次连续而流畅地从传说中的古代前进到历史政治:
以编年体顺序,细节化地描述关于国王与族长的所有重要事件,包含他们与罗马人、不列颠人、丹麦人与诺曼人的数场战争的真实记载;用图像方式描绘克朗塔夫(Clontarf)战役,“强弓”(Strongbow,1130-1176)的入侵;国王罗德里克·奥康纳(Roderick O’Conor,约1116-1198)之死;爱德华·布鲁斯(Edeward Bruce,约1280-1318)加冕为爱尔兰国王;奥尼尔家族(O’Neills)与奥唐纳家族(O’Donnells)对抗英格兰的战争;征用阿尔斯特(Ulster);克伦威尔(Cromwell,1599-1658)的入侵;迫害天主教徒;詹姆斯(James,1633-1701)国王即与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1650-1702)之间的战争;德里(Derry)围攻战与博伊奈(Boyne)战役;阿斯隆(Athlone)围攻战;奥格里姆(Aughrim)战役;利默里克围攻战与《利默里克和约》;刑法;志愿军;爱尔兰人联合会;1798年起义;联合;天主教解放与废止令;青年爱尔兰运动;芬尼亚会起义(Fenian insurrection);土地同盟(Land league)等等。
进一步的例证出现在1875年。乌利克·伯克(Ulick Bourke,1829-1887)以马克斯·米勒(Max Müller,1823-1900)的风格出版了一本有关爱尔兰文化的语言考古论著。他自命不凡地将之命名为“盖尔人的种族与语言之雅利安起源”(The Aryan Origin of the Gaelic Race and Language)。该书竭力把现代种族人类学与本土的、吟游诗人式的神话学结合起来,并着重提出了下列棘手问题:“伊特鲁亚人是盖尔人吗?盖尔人的子孙拥有雅利安人的血统,而非迦太基人或腓尼基人的血统吗?”由此,17-18世纪典型所承载的那种东方主义考古模式与19世纪的科学印欧模式之间的根本矛盾及范式冲突,得以被转移——在形式上完全不像史学上的“竞争原则”——最终被融入为一种黑格尔式的“扬弃”。
如此史学著作面向的是更为广阔的市场,通常针对美洲的爱尔兰移民。但是,即便是那些由爱尔兰本国学界所完成的更为严肃的史学著作,同样显示出一种趋向:即通过给出一种神话般的导论,并时常将之掩饰为一种对已有文献的概览,来为史学论著设置场景。在尤金·奥库里(Eugenne O’Curry,1794-1862)完成的多卷本里程碑式巨著《古代爱尔兰人的风俗和习惯》(O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Ancient Irish)中,在作者身后担当编辑之责的W. K. 苏利文(W. K. Sullivan)写下了一段冗长的导论(1873年)。他详细阐述了从格林到马克斯·米勒的整个文献学的“调查状况”(status quaestionis),以便确定该国盖尔人的种族构成。苏利文从当地传统中吸收了如下观点,认为,“大不列颠与爱尔兰都先后为不同种族所居住”。接着,他拒绝了除此以外的这些自相矛盾的传统,认为它们是无价值和不科学的:
在任何情况下,时间很少被用来认真探讨与分析由莫尔人(Umorians)、佛莫尔人(Fomorians)、尼美第人(Nemedians)、费尔伯格人、达努神族、米利都人及其他族群的一连串奇特神话。而正是这些族群构成了爱尔兰历史的神话部分。
最终,本土的“起点”神话如今同现代文献人类学相协调,以便提出如下观念,即认为,侵入此地的印欧语族凯尔特人(高个、金发)驱逐了该国前印欧语族的定居者(矮个、棕发)。这种模式仍于20世纪初在约恩·麦克奈尔(Eoin MacNeill,1867-1945)完成的重要考古著作中占主导地位。的确,麦克奈尔业已对史学中的“种族”概念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怀疑。他认为,这一概念“经常是以非常随意且存在极大误导的方式存在于流行写作和讨论中”。然而,他颇受欢迎的系列讲座“爱尔兰历史的各阶段”(Phases in Irish history),却仍然在其结构中追随着业已建立起来的范式(1:“古代爱尔兰人:一种凯尔特人”;2:“凯尔特人殖民爱尔兰和不列颠”;3:在凯尔特人之前的爱尔兰定居者)。此外,他在其更全面的著作《凯尔特的爱尔兰》(Celtic Ireland,1921年)中,开篇本身使人感到有必要把历史事实从一个神话盆地中拖出:
有关爱尔兰早期历史的常见描述告诉我们,在大约公元前16世纪左右,该岛被盖尔种族所占领。在此之前占领该岛的是达努神族。再之前,则是费尔伯格人。
有关古代爱尔兰的历史书写,或许到帕特里克·维斯腾·乔伊斯(Patrick Weston Joyce,1827-1914)才成熟起来。他是前文提及的《古代爱尔兰社会史》的作者,后来又撰写了大量富有影响力的著作,如《爱尔兰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Ireland)和《简明爱尔兰史》(A Concise History of Ireland)。乔伊斯还选择了一种史料考证性的开头(incipit)。如同在其之前的奥库里一样,他首先调查爱尔兰早期历史中的现存史料:即本土编年史和中世纪史书。他在仔细回顾这些史料中包含的传说资料后,逐渐转向中世纪晚期更可信的档案材料,开始讲述亨利二世(Henry II,1133-1189)与约翰王(King John,1166-1216)的征服,并由此把他的叙述带入事实性史料。只有在乔伊斯著作所带来的风潮中,对本土传统进行的文献学研究、对于考古证据进行的事实性研究及历史之书写等模式才匹配到一起。不过,神话与事实、本土传统与史料档案之间更为古老的含糊关系,却仍然统治着流行中的重印本。史前与历史之间的复杂过渡期,以及有关前者如何为后者“设定场景”的问题,仍然纠缠在一种本土的、前现代的、半传说式的史料传统中。当20世纪的考古学家试图在爱尔兰建立史前人口范式时,他们又退后到古代编年史所使用的那些术语中。极受尊重的T. F. 奥拉希利(T. F. O’Rahilly,1883-1953)便把爱尔兰的史前定居视作一连串前后相继风潮的组合产物。其中,他指出的族群有:布立吞人(Pretanic)、比利其人(Bolgic)、伦斯特人(Laginian)和戈伊德尔人(Goidelic)。即便本土神话学的证据是无法估量、不可相信的,但我们也无法忽略或拒斥整个神话。从19世纪爱尔兰考古学的奠基者乔治·佩特里(George Petrie,1790-1866)直至今天,爱尔兰考古学家都在竭力协调本土编年史中的神话表述与来自实物发现的国际范式。
爱尔兰的历史学家从未发现自己在开启民族史学时如米什莱风格那样拥有“宏大场景”,也未曾如德意志模式那样呼唤一种历史黎明的永恒原始状态,亦未曾如比利时模式那样拥有一种交通、交流与相会的感受。这源于三个因素叠加而成的结果。首先,爱尔兰远远超出了古典或后古典历史学家的视野,除了在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4或63-约公元24)、索里努斯(Solinus,约3世纪)和比德(Bede,约673-735)著作的一些注释中可见踪影。它在罗马帝国外的特殊位置,同样意味着,有关其早期历史的记载,除了本土神话资料外一无所有。第二,它在12世纪被英格兰军队征服。这阻止了任何本土成长起来的人文主义者或对该民族过去加以学术研究之举的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游吟诗文献被压缩为受到重重包围的传统主义,不断以一种反英格兰的反抗姿态,重复其伪历史性神话。第三,“征服”这一概念已成为前盖尔、盖尔与后盖尔定居的一种嵌套修辞方法,象征着民族延续性的对立面。相反,在爱尔兰历史书写的修辞中,一种非叙述性开头,并不表现为该国的景观或史前情况,而是表现为对神话和传说的召唤。在不知不觉中,19世纪的爱尔兰民族历史学家追随并强化了如下观念:爱尔兰是一个奠基于神话和永恒幻想而非历史时间的国家。再者,他们总是通过“从最早时期到当代”(如同许多副标题都以各种方式包含这些内容)的叙述时间范畴来进行追溯,从而推后了一种历史终结感,并把恰当的历史终点(finale)定位于一种经常迫在眉睫、但从未实现的未来视角。在这里,与其他方面一样,对叙述策略的形式分析似乎明显突出了历史文本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并在文本上使之具体化。反之,这一点也表明,这些倾向依靠互文式回应与叙述惯例代代相传,经常超越大量突变与中断,始终保持着活跃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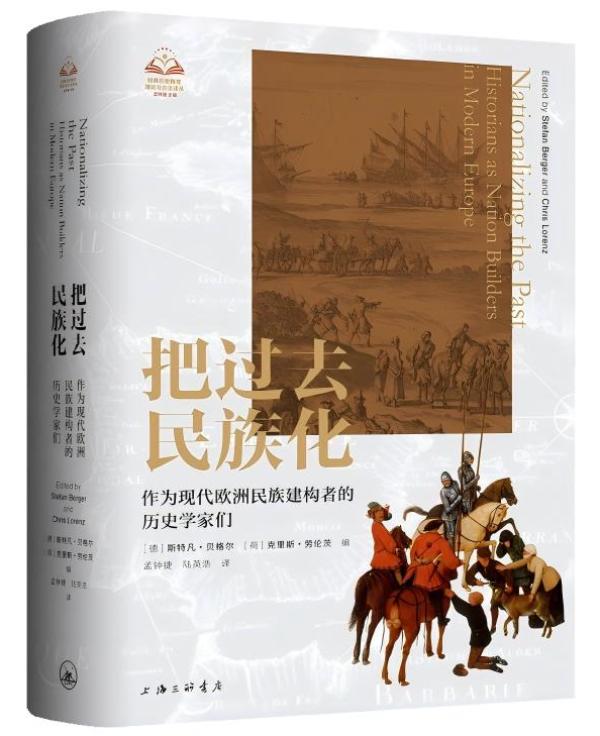
(本文摘自《把过去民族化:作为现代欧洲民族建构这的历史学家们》,孟钟捷、陆英浩译,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9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