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1年11月开始,“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开始通过访谈与书评的形式介绍美国学界对韩国流行文化(尤其是K-pop)的研究。三年过后,这些介绍已经形成了一定影响,不仅有部分内容被翻译成韩文在韩国再次发表,其内容也影响到了国内一些高校里传媒与社科专业研究生的论文选题。然而,正如之前有读者反映,这些关于韩国流行文化的评论高度以美国为中心,折射出以韩裔美国人为代表的美国亚裔群体通过韩国流行文化表达的诉求。
添加微信好友, 获取更多信息
复制微信号
在去年7月,“澎湃新闻·思想市场”采访了英国V&A博物馆韩国策展人罗萨莉·金,谈论她举办的《韩流!》特展,这带来了部分欧洲视野。这次,“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对首尔国立大学韩流研究中心(Center for Hallyu Studies)主任及传媒系教授洪锡敬进行了专访。洪锡敬在加入首尔国立大学前,曾在法国波尔多大学任教多年,对包括韩剧与K-pop在内的韩国流行文化在法国的情况有深入的调查与研究。2020年,洪锡敬在首尔国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防弹少年团在路上》一书的韩文本,2023年同社推出了英文翻译版,目前已被翻译为日文、越南文、印度尼西亚文,其法文版今年7月刚刚出版。在书里,洪锡敬带来了以法国为主体的视角。刚刚过去的巴黎奥运会上,法国再次成为世界的焦点。同时,今年也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诸多以中法文化交流为主题的活动正在举办。与此同时,尽管没有官方背景,韩国流行文化已经悄无声息地在法国浸润多年,带来法国的韩语热与韩国研究的发展。此次访谈围绕韩流在法国与欧洲的状况展开。

《防弹少年团在路上》韩文版与英文、法文、日文译本
澎湃新闻:现在的K-pop研究里,防弹少年团无疑是主要话题之一,但您的书是在2017、2018年开始写的,当时BTS还远远没有那么火,促使您研究BTS的契机是什么?
洪锡敬:我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数字文化与全球化是如何交融从而改变跨国流动的。我的第一本书《全球化与数字文化时代的韩流:浪漫满屋、江南STYLE及之后》(세계화와 디지털 문화 시대의 한류:풀하우스, 강남스타일, 그리고 그 이후)是关于韩剧在法国的接受。在我加入首尔国立大学前,我在波尔多大学任教。在那时,我已经知道我的第二本书会关于K-pop。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K-pop开始爆发式呈现,包括我在内的从事全球传播研究的学者都意识到其媒体影响力。我对防弹产生兴趣则是我因为注意到他们的《Skool Luv Affair》与《最美花样年华》专辑里的跨媒介叙事策略。我那时感兴趣的是他们在做什么,但他们的专辑开始在美国流行,有了国际排名,在美国节目里出现。在那时,根据他们在音乐视频里的评论与调子,我可以观察到,他们在K-pop里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在那个时候,K-pop主要还是东亚现象。和BTS或K-pop有关的文化现象都是通过网络传播的。我对此很熟悉,因为我关于韩剧在法语世界的流传的书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韩国流行文化需要进入他们的群体与系统。因此,我意识到,相比其他团体, 防弹开启了将全球作为目标的新道路,我们可以用全球来定义他们。正如我在书里说到,我见过方时赫,在准备韩国广播公司《明见万里》(명견만리)一个特别节目的时候,他了解了我的研究后表达了接纳。而就这本书而言,我做了一年田野,进行了一年的写作,用八个月进行了四次重写。我想让这本书能为公众所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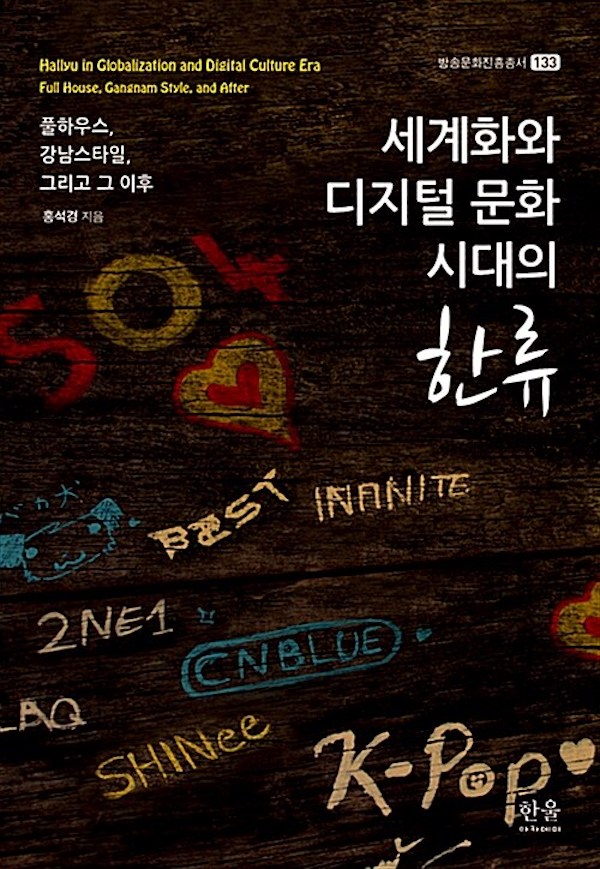
《全球化与数字文化时代的韩流》
澎湃新闻:就您早年对韩剧与韩流的研究,根据您的研究经历与观察,现在的K-pop主导的韩国流行文化与早年韩剧主导的韩国流行文化更多是延续还是断裂?
洪锡敬:我可以很清楚地说,这是一个延续。在文化上断裂是很难的,延续是常态。当然,发生变化的是媒体环境。在我的课上,我一般会讲授韩流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韩流的东亚阶段,主要的媒体是广播电台,在国际市场上传播相关节目。在这个过程中,韩流在日本、中国与东南亚流传。第二个阶段是我在我之前书里分析的,韩流的数字化与全球化阶段。而第三个阶段从2016年开始,因为在这一年,韩国失去了中国大陆市场。但与此同时,奈飞进入韩国,开始对韩国市场进行投入。因此,韩流进入了平台阶段。但是,之前的媒体环境没有被打断,反而是互相支撑,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媒体环境被平台所更改。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延续,只是拥有不同的媒体环境。
澎湃新闻:在目前英语世界的K-pop研究里(由于您的书已经翻译成英文,也完成了其进入英语学界的仪式),您的书独树一帜之处无疑在于欧洲视角。您在书中一开始就提到了2011年SM公司在巴黎的演唱会,根据我做K-pop田野的一些经历,通过您的细致描写,已经感受到K-pop在欧洲的一些潜在特点。您认为K-pop在欧洲,特别是法国,相比美国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SM公司2011年在巴黎的演唱会
洪锡敬:SM在巴黎的那场演唱会不仅仅是一个欧洲的事件,首先这是一个K-pop在国际上的盛大展演,在此之前,没有这样盛大的K-pop展演,我也不认为在此之前美国举办过KCON。与K-pop展演相伴的,还有对韩国其它方面的兴趣,比如韩料。与此同时, 也与地方的粉丝团体相联系。在准备过程中,SM并不确定他们能取得这样的成功。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预订的场所并不大,我记得只能容纳6000人左右,但在开票一分钟之内,所有的票都卖出,同时票价非常贵。这个演唱会也成为了世界上有很多人听K-pop音乐的一个证明。而就K-pop在法国的特点而言,法国非常自豪于自己的文化多元主义,与英美的多元文化理念非常不同,后者的文化多元主义是基于社区。而法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共和国,只有一个国民认同,但公民们可以拥有各种文化背景。这有一些虚伪,实际上法国存在种族主义,但在公众话语里,却不允许问族群背景,这会被看作是反犹主义。在法国,公开的反犹主义舆论是违法的。不过,在这样的文化多元性背景下,也有了某种世界主义的审美,相比之下,法国人对外来文化更加开放,所有的好电影——即使是外国电影——都在法国不断有观众。一些更小众的电影也在法国有市场,比如印度、越南和尼日利亚电影。这样的文化多元主义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这对于发展出多文化感非常重要。在我的第一本书里,我对法语世界的人对韩剧的接受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大家消费韩剧之前,已经开始接触日本流行文化。法国的韩剧粉丝在观看韩剧时,他们已经看过了日本漫画及改编的动漫(第一批在法国上映的韩剧同样是由韩国漫画改编的)。是他们对漫画的兴趣导致对韩剧的兴趣。一些人对日本动漫和漫画的兴趣长达二三十年,是这个群体最早接触到韩剧。我认为这在西班牙、意大利甚至德国也是如此,最早的韩剧粉丝是日本动漫粉。日本之外最大的动漫市场是法国而非美国。看一下法国有多少人口,就能明白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们的日漫粉丝基数是巨大的,这也为法国人接受韩国流行文化奠定了基础。

法国的动漫周边店
澎湃新闻:您在书里从阶级、种族与性别三个方面展开研究,种族与性别(尤其后者)无疑是英语世界研究K-pop主要的两大视角,但阶级方面还比较欠缺,但这在欧洲无疑更重要。您在阶级这一章里详细描写了法国战后社会变迁与社会阶层固化对年轻人接受K-pop的影响,您能不能介绍下阶级在K-pop在欧洲传播中的作用?
洪锡敬:不仅仅是我的研究,在文化研究里,我们都会用阶级、种族与性别这三个视角来分析社会、政治与文化现象。当我提出这三个问题时,我问的是,在韩流里,阶级虽然存在,但这是隐性的,我试图去发现阶级视角是怎么被隐藏起来的,是以什么另样的面孔呈现出来。而就韩流而言,阶级问题通过代际沟通问题呈现出来。作为一名好的K-pop粉丝,你需要有一定的购买能力,去购买一些周边产品。尽管你可以在油管上免费听K-pop,在没有购买能力的情况下,你是无法进入粉丝的集体和参加粉丝见面会等。K-pop的受众以中产阶级与中产阶级上层为主,K-pop的粉丝文化是非常中产阶级的文化。我也会观察欧洲特别是法国的粉丝们的父母怎么看待孩子的追星问题。作为电子流行文化的消费者,K-pop粉丝不仅跳舞还学习韩语。他(她)们有购买力,他(她)们的父母有财力支持小孩去追星。除非是极个别案例,这些粉丝们一般没有酒精、色情甚至毒品和暴力问题。总体上,K-pop文化是非常中产的。
澎湃新闻:就种族方面,您在以前的《防弹少年团开辟从未有人走过的道路》(这篇文章已经翻译成中文,发表在《韩民族日报》上)一文中就高度评价了K-pop对亚洲人的世界形象的意义。在这方面,您和高玉蘋视野一致。我之前采访过高教授,她是从她长期研究种族社会学与亚裔美国人的角度得出这一观点,不知道您是从什么角度得出这一结论,认为K-pop不仅仅是作为民族国家的韩国的名片也可以是世界亚洲群体的名片?
洪锡敬:当我在研究韩剧在法国与法语人群中的接受时发现,甚至是从越南移民到法国的荷蒙族人(Hmong)——他们居住在布列塔尼地区,我和他(她)们交流过多次,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这一族群的青少年都会通过韩国流行文化来重建他们的亚洲族群性,我非常震惊。比如,我从他(她)们那里听说,阿姆斯特丹的亚洲狂欢派对充满了K-pop和多元文化的亚洲年轻人,大家在派对上跳舞,这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特别是在疫情期间,由于许多西方人——尽管这样说有点泛化——分不清中日韩三国人,防弹少年团成为了对亚洲人种族歧视的众矢之的,特别是德国一个电台通过对防弹的评论表达了很多对亚洲人的仇恨情绪。尽管我们没有足够多的机会通过田野去观察美国的情况,但可以说,K-pop为东亚的年轻人们创造了非常积极正面的形象。但这也产生了一些内部的等级性,比如认为东亚人比东南亚人好看,我们需要对此警醒,但是根据我多年观察,我可以说K-pop对东亚青少年产生了很多积极影响。
澎湃新闻:就亚洲人在法国而言,您在书里简单提及了法国的中国热(Chinoiserie),我认为程抱一、程艾蓝、赵无极、朱德群等华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法国主流文化界的影响力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作为法国的东方主义另外一方面,正如您提到,很多法国人对日本文化有特殊情结,特别我之前在巴黎也注意到日本动漫在法国非常有影响力。不知道这是否对K-pop在法国传播有所促进作用?
洪锡敬:法国的日本热叫做日本主义(Japonisme)。法国的中国热是在17和18世纪,法国对日本的兴趣则开始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些兴趣是通过法国知识分子发生的。而在流行文化领域,我并不清楚大家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韩流是自下而上的现象,普通民众特别是边缘化的青少年对其的接受,在知识分子们开始对其关注前就开始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到现在,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其它欧洲国家,韩流还是需要被严肃对待为重要的文化现象。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欧洲知识分子们没有接触到这些文化,他们需要去理解并接受。尽管他们不得不接受,他们不会喜欢。有很多理由,他们不喜欢韩流,这对于他们来说不“酷”。我认为这一矛盾不会轻易消失,而是会继续存在。因此,法国中国热、日本主义与韩流有很大区别。其中,韩流有潜力去改变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可以是在文化或社会层面,而在一些国家,韩流在政治上很有影响,大家可以通过韩流被动员起来,去实现一些目标。尽管我们要关注韩流会不会在一些地方导致重要事件,但这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在现在青少年都非常对政治冷漠的情况下。总体上,对韩流的兴趣是人民的选择,而不是知识分子根据自己美学与喜好变化带来的影响。

展现法国日本主义的绘画
澎湃新闻:在另一方面,作为阶级与种族问题的交汇点,法国相比英国等其它欧洲国家有更浓厚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学术界也相对英美更加保守。您在书里提到了K-POP流行导致像巴黎七大这些传统学校开始越来越接受韩国研究,这在美国也是一样的,韩国流行文化研究在美国越来越有主流地位。我认为您的硕士学生被芝加哥大学东亚系博士项目接受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件,在美国名校里,芝大一直是相对保守的(同时芝大也是美国学校里与法国学术界合作最强的学校)。K-POP对法国的韩国研究有没有类似影响?
洪锡敬:法国大学没有美国大学那么多资源。在法国,高等教育以公立为主,大家都可以入学。学界没有相应的资源去拓展韩国研究。然而,学界还是在增加相应的教席位置,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在其它领域,学界一般都在减少位置。非常清楚,这是学校在回应学生方面日益增多的需求,大家想主修韩国研究。这不仅仅是法国的现象,是全欧洲的现象。甚至在印度也是如此,在印度,大家为了进入韩国研究系,竞争无比激烈,录取率只有千分之一。因此,进入韩国研究的也是非常棒的学生。这些变化在真正地发生,而其结果在每个国家会有所不同,因为大家有不同的大学体制。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学生们给学校施加压力,去改变其体制。在Duolinguo上,韩语是第四受欢迎的语言,前三名是英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这是非常新的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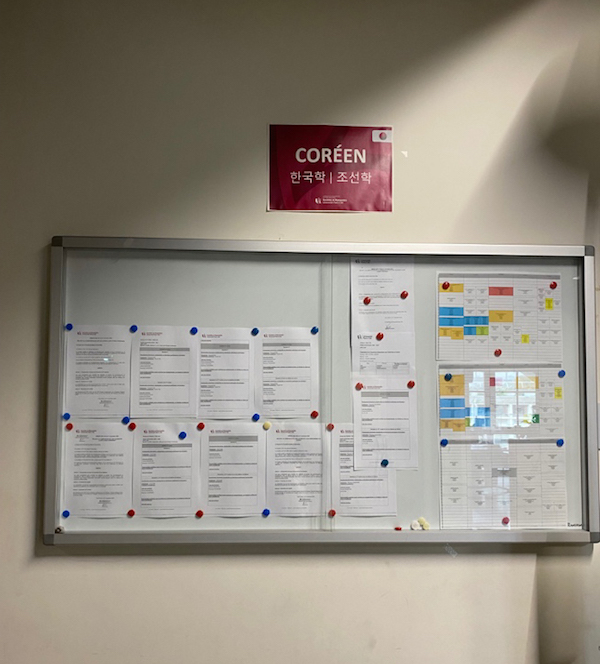
巴黎第七大学的韩语课程表
澎湃新闻:就种族话题,您在书里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韩国记者非常热衷于强调欧洲的K-POP粉丝是白人为主体,而非少数族裔,我认为这和美国的情况有些相反。我在芝加哥观看过一场韩舞翻跳活动,参与者以少数族裔为主。而一位参加过英国韩舞翻跳的中国留学生告诉过我,比赛中基本是英国白人为主。不知道您认为是什么造就了这一差异?
洪锡敬:你可以就此写一本书。我认为,在法国,有很多多文化族群的青少年对K-pop感兴趣,他们也翻跳韩舞,但他们没有那么显性,他们拥有相对少的资源,因而不那么容易让自己在油管等平台上被看见。正如我已经说过,K-pop是非常中产的现象。现在,很多中产小孩都有能力将自己作为K-pop粉丝的身份表现出来,但伴随着防弹与韩国文化产业的兴起,K-pop粉丝不再是一种负面的标签。在各个城市的市中心的韩舞活动是非常重要的现象,尽管现在的青少年通过占有市中心物理空间进行自我呈现的动力有所减少。我认为K-pop显然是一种另类的文化形式。的确,K-pop里的白人中产青少年粉丝正在上升,他(她)们在这一运动里呈现自己,但这不意味着少数族裔群体没有参与进来。在美国,种族与性别的交叉是重要的社会与文化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欧洲没有那么显著。我认为,在美国,有更多的黑人与拉丁裔青少年用K-pop去表达自己的认同。正如你已经说过, 在欧洲,阶级问题更重要,因此与K-pop相关的中产阶级青少年文化形成就显得更加显著,而种族与性别因素就被边缘化。
澎湃新闻:就性别话题,您一直是“软性男性气概”理论的提倡者。一些研究传统东亚儒家的学者会把“软性男性气概”与东亚传统文化联系起来。比如香港大学的宋耕教授在为他关于明代儒家的《文弱书生》一书中文版的序言里把K-pop里的软性男性气概与明代儒家书生理想,及其对朝鲜王朝的影响,以及两班制联系起来。我认为这是非常有趣的视角。您知道,关于K-pop里的K是什么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您是否认为在软性男性气概方面,包含着传统意义上K-pop的韩国性与亚洲性?

《文弱书生》中译本,香港大学出版社
洪锡敬: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笑)。你大概知道东亚传统里文与武的关系,关于软性男性气概问题,非常复杂。就韩剧而言,是去关心别人,这非常靠近传统儒家的礼节,在日常生活里体现。我们需要关心别人,但又不是西方社会学意义上的他者性。当有人在我面前、在我身边出现时,在我们考虑自身之前,我们需要先去考虑他们。当我们说话做事时,我们需要考虑对方的感受。这的确是我们在以儒家为基础的明代中国可以看到的。当然,我们不清楚宋耕教授是在何种基础上找到儒家与韩流里的软性男性气概的关系。在韩流里,这种对别人的关心是很明显的,无论是在韩剧剧情里,还是在K-pop艺人与练习生的日常生活里,抑或在他们与粉丝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公共关系里,都是如此。然而,我认为,K-pop属于剑的文化而非笔的文化,这是一种规训的文化,对身体的运用非常重要。而在明代中国的儒家理想里,身体是用来呈现一种对他人的态度,是一种对礼节的展示,这一理念不是以身体为中心的。因此,我认为在K-pop里,对身体的规训非常重要。大家展示非常协调的舞蹈,对日常生活的约束,还有大家的化妆习惯。在韩国,我们将男团偶像看作新罗王朝的花郎(Hwarang),即来自贵族家庭非常受规训的年轻的花美男。尽管我们不想用这样的军事话语,在这种晚期资本主义的娱乐公司体系里,没有谁真的逼着他们去做任何事情,他们是一种自我练习和规训,或者说是自愿成为练习生和艺人。为了在每天的竞争中表现优异,他们需要保持高度的自我管理,同时也按照传统韩国儒家理念的要求,他们需要遵守礼节,需要在粉丝面前有礼貌。因此,我部分同意宋教授的观点,我希望阅读他的书,但我并不认为这与明代中国存在有意义的关系,因为在朝鲜王朝,主导的男性气概是非常压迫的。我们无法非常简单地将这种后现代的东西与明朝和朝鲜王朝建立联系。我们需要将它们放到不同的阶段里。

2016年韩国历史电视剧《花郎》剧照
澎湃新闻:就法语世界而言,您有没有注意到通过K-pop在法国的流行再传到世界其它地区的情况?我在中国西南地区做过一些韩舞翻跳的田野。在我田野一开始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件,两年前在我家乡昆明由法语联盟举办的一场法国夏季音乐节上,有数支韩舞翻跳节目。我了解到这些节目是一个中法合资的舞蹈工作室组织的,工作室老板之一是北非裔法国人。昆明是云南的省会,位于越南的北面,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是滇越铁路,从河内通往昆明。这是越南在19世纪末成为法国殖民地后,试图将影响力深入中国西南地区的结果。在20世纪上半叶,云南很大程度是法国的半殖民地。而那场法国音乐节就在滇越铁路旧址上进行,我认为是一个很典型的后殖民景观,而在中国与法国香颂(chanson)与古典音乐等节目中穿插出现了韩舞节目,我认为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在滇越铁路上举行的法国音乐节里的韩舞表演
洪锡敬: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与越南的学校有一些关系。就我所知,K-pop在越南非常火。但总体上,我还没有机会去观察K-pop怎么在法国的框架下在其它国家出现。你应该就此写篇论文,这将是非常有趣的个例研究。现在,我们有太多的关于K-pop的接受研究,关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案例,但没有什么理论含金量。然而,你说的将是一个真正的案例研究。
澎湃新闻:您的田野更多是在巴黎地区进行,后来我从昆明那家舞蹈工作室的中方创始人(她们还有一位泰国创始人)处了解到在法国南部小城尼姆,她也见过20多人在进行韩舞翻跳,韩舞的世界影响力让她非常震撼。不知道您有没有在巴黎以外观察到K-pop的相应流行情况?
洪锡敬:当然!在法国各大城市,你都可以看到K-pop。我曾经在波尔多大学任教,那里有非常有趣的K-pop粉丝基础,有韩舞随机跳。在网上,我们可以找到以在法国各大城市为背景的韩舞翻跳视频。
澎湃新闻: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您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韩国。您在书里提到了方时赫及防弹成员希望去首国大的废弃游泳池却被保安拦截的趣闻,您也提到后来是学校提名方时赫作为杰出校友回来。就BTS的音乐视频里与欧洲传统文化的关系,无论是《血汗泪》里面的文艺复兴艺术与尼采引言还是《狄奥尼索斯》里对古希腊悲剧的化用,有学者认为这和方时赫在首国大学的专业是美学有关。我还听说过,在方时赫在首国大读书时,作为日本殖民遗产,首国大包括美学在内的文科仍然有强烈的德国学术传统影响。作为首国大之前的学生与现在的教授,不知道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进一步强调的?

《血汗泪》在音乐视频叙事与文艺复兴图像叙事里建立跨媒介联系
洪锡敬:除了《血汗泪》与《狄奥尼索斯》外,还有《春日》,都有非常多的艺术呈现。现在,除了防弹外,甚至其它韩团都在这一方面发展。这是韩团在这些年发展出的一个策略,这让粉丝们更感兴趣去深挖视频文本里的东西,大家试图去讨论里面这些意象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去问,K-pop为什么不用中国和日本的东西,而用欧洲和希腊的东西。里面有德国的东西、法国、西北欧的东西,甚至还有狄奥尼索斯。这可以让视觉文本甚至歌词显得与众不同。的确,方时赫发起了这一策略。但我也认为,这是由集体发展起来的,大家进行讨论,去讨论各种方案。我们无法确认,每一个古典意象来自谁的观点,这是一个黑盒。然而,这种在防弹那里最早出现的美学和歌词策略,主要是方时赫发展出来的,他是主要的制作人。同时,方时赫在首国大时,美学学科的确有德国强烈的影响,同时也有法国哲学的影响。总体上,我们的确有一些在德国美学领域很重要的学者。

方时赫在首国大做演讲
澎湃新闻:您在书里还提到您2015年和方时赫关于跨媒体的讨论,当时方时赫对这个概念很陌生,但现在跨媒介已经成为韩国娱乐公司人员的口头常挂名词之一。您是否认为这是学术研究对韩国娱乐界的影响?或者从更大的角度而言,您是否认为韩国娱乐公司制作人会关注K-pop方面的学术讨论(包括您自己的研究)?
洪锡敬:我不太确定。在那时,我的确惊讶, 方时赫并不了解跨媒介这一概念,尽管他本身是跨媒介的实践者。我认为,在K-pop产业界,每一项事务、每一种策略和生产方式都会迅速传播,很快被其他制作人和娱乐公司运用。同时,大家互相都认识,都是朋友,也相互竞争。比如A为HYBE公司工作,B为JYP公司工作,但其实双方都认识。比如说,我的许多之前的学生在不同大学找到教职,同时也有一些硕士生进入娱乐行业。就跨媒介这一概念,尽管他们一开始不知道学术界这样称呼这一实践,但通过观察美国流行文化,比如漫威宇宙,他们学到了跨媒介的方法。但是,一旦他们知道了这一做法,就变成了他们的实践,无论是否意识到这叫跨媒介,在不同娱乐公司里就会很快流传起来。这只是一个案例。现在的K-pop产业界,新的做法与元素会很快地互相影响,这是一个很小的圈子。我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也是关于K-pop的生产系统,对生产者进行研究,韩流创造经济系统最有趣和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生产系统。生产者们不是一个很大的世界,大家一直互相交流,可能是邻居。比如《釜山行》这部电影,里面的僵尸是由街舞舞者扮演的,因此创造了新的僵尸场景,他们动得很快、非常有效。就像K-pop产业人们聚集在一起,很多东西出现得很快。
澎湃新闻:与此同时,教育社会学对法国的大学校(grande école)系统进行了广泛研究,该系统为满足国家需求而在大学体系之外培养专门人才。同样,K-pop产业似乎正在履行类似的角色。据我所知,许多韩国家长将他们的孩子加入四大娱乐公司成为练习生视为上SKY大学的替代路径。您认为K-pop练习生系统可以被视为韩国版的大学校系统吗?

法国国庆节阅兵中出现的由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学生组成的仪仗队
洪锡敬:我不这样认为,两者没有相似之处。法国的大学校是由拿破仑建立的,去教育青少年去为国家服务。但是,K-pop的发展没有从国家分到蛋糕。韩国国家希望把自己呈现为对K-pop发展很有帮助,但这只是任何发达国家都有的对文化的资助。比如,当有韩团进行世界巡演和租借场地时,大家需要钱,但不清楚所有票是否能卖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些微薄的资助。但是,如果说,K-pop的练习生系统如果想从政府那里拿到资助,那完全是不可能的。许多外国学者希望找到证据证明韩国政府资助韩流文化产业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但这种证据并不存在。事实是,在韩国政府开始感兴趣前,韩国的文化产业就取得了成功。韩国政府仅仅是需要利用这一成功去打造国家形象,很多部长都喜欢做这样的事。这与法国大学校模式完全不相似,甚至韩剧与韩国电影都不是这样。
澎湃新闻:最后一个问题,今年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故宫博物院正在举行一个凡尔赛宫与紫禁城交流的特展。我认为中国和法国相似之处在于,在塑造对外形象上,都喜欢强调自己的传统文化。法国哲学家冉-卢克·马里翁(Jean-Luc Marion)在多年前访华时的一次访谈里,也说过法国和中国相似的文化普世主义与发达的文人文化。一位在中国媒体工作过的朋友和我说,韩国是文化立国,而文化不是中国的重点。我认为她指的是流行文化。或许可以说,中国对外文化宣传路径更像法国,而韩国似乎更像战后的英国,更依靠流行文化塑造自己的国家形象。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包括K-POP在内的韩国流行文化在韩法交流里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洪锡敬:我不太清楚K-pop在韩法关系里起到什么作用。对于法国政府,我不认为韩国是重要的,这只是一个法国销售高铁的市场而已。另外,韩国人也购买法国的很多奢侈品,法国也是韩国的一个旅游地点。然而, 我并不认为法国官方很重视韩国。另外,认为流行文化是韩国政府的重点,这是不对的。我可以给你无数的例子。在韩国,我们没有专门为K-pop演唱会设置的表演场地。你如何解释这个现象?我们没有为K-pop设计专门的基础设施。因为韩国官方认为K-pop的浪潮很快会过去,会丢掉国际市场。政府会考虑,在此之后,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无法用其来赚钱。对于韩国政府,K-pop是一种赚钱的文化形式,比如卖专辑,也可以帮助出口汽车与三星手机。这对于韩国产业有帮助,也有助于韩国国家形象塑造。就到此为止了,韩国政府在文化层面对K-pop没有兴趣。这也是我们一直批评政府对流行文化态度的地方。在朴槿惠政府期间,政府甚至制定了文化创作者的黑名单,因为很多韩国文化创作者们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是左派,像朴赞郁这样的著名导演、《寄生虫》的导演奉俊昊、《鱿鱼游戏》的导演黄东赫,刚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韩江,还有一些演员。韩国文化部不会为这些导演提供资助,同时进了黑名单的演员也没资格参与韩国政府资助的片子的表演。因此,我不认为文化是韩国政府的优先考虑,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韩国流行文化完全是产业人与从业人员的功劳。而韩国相对中国甚至日本的优势是在文化创作里可以发挥的空间更多。通过韩国1980年代的运动,以及流行文化在1990年代的兴起,韩国人民甚至是右翼,都认识到文化表达的价值。这是韩国发展文化产业的主要优势和能量所在,而不是政府有多支持。
(在采访问题准备中,昆明旦斯特舞蹈工作室Phoenix女士提供了观察到的在法国韩舞的情况,在此特别感谢。)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