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气候特使托德·斯特恩
添加微信好友, 获取更多信息
复制微信号
11月1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九次会议(COP29)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正式拉开帷幕。
时光倒转到九年前的2015年12月12日,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的最后一天,全体会议厅里,法国外长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冷静地阐述着当天的计划——那一天将以通过《巴黎协定》为最终目标。
时任美国气候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坐在那个大厅里,他突然意识到,这项旨在促使全世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里程碑式协议,要实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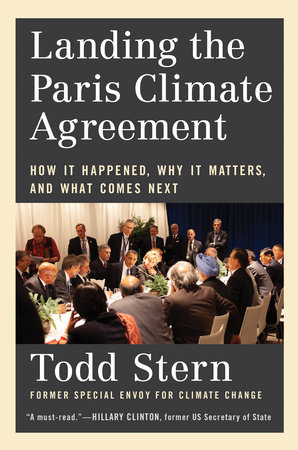
“那一刻,我不禁哽咽了。”他回忆道。
该如何形容这个过程?是巴黎大会日夜紧张磋商、争论和游说的14天;是2011年南非德班会议确立巴黎谈判任务后,不断筹备和调整战术的4年;是中美领导人2014年在北京发表历史性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是2009年斯特恩作为奥巴马政府首席气候代表后率领团队在气候谈判桌上与各方全力以赴的7年;是从1995年第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起,世界各国为达成一项具体、有效、可操作的气候协议而努力前进的1/5个世纪——而这一切,终于在巴黎的冬日看到了成果。
《巴黎协定》最终得到了171个国家的签署,确立了明确的目标:到本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努力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每个缔约国根据自身国情,自定减排目标和行动计划。
从内容和规模上来说,这是一项极难达成的协议。此前漫长的20年里,每一届气候大会都在以此为目标进行谈判,但始终难有突破性的成果。1997年,COP3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采取行动减少排放,但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设定强制性承诺。这种“自上而下”的减排机制引起发达国家的态度普遍消极,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更是在2001年便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义务”为由拒不参与其中。
2009年的COP15更是被视为有史以来分歧最为严重的大会之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评价称,这次会议甚至连“逗号”都算不上,顶多是个“冒号”——意思是“现状总结”加“请听下文”,寄希望于未来能够达成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
也是在那一年年初,斯特恩被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为该国首位气候变化特使。那时,他没有设想过《巴黎协定》形成的可能性。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2009年哥本哈根的谈判中,他尽力确保协议能够同时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打破《京都议定书》中的“防火墙”,获得更普遍的全球参与,却亲身参与和见证了最终混乱的收场。
作为中美气候谈判的重要参与者,斯特恩也一直致力于推动中美双边气候合作关系的发展,并与中国前气候特使解振华缔结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他很有力量,但又很幽默。”斯特恩如此评价自己的谈判对手。他认为,当双方能够真正倾听对方的意见,并试图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时,合作会变得更加顺利。
2013年4月,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成立。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发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将携手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致力于达成富有雄心的协议,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这给次年的巴黎谈判注入了很大的信心和动力。
《巴黎协定》是一个关键的开始。在复杂、动态的国际利益格局中,这样一份来之不易的多边主义外交成果既是成功的,也是脆弱的。2024年11月6日,曾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前总统特朗普二度当选;此前他曾称上任后将再度退出该协定。
在《巴黎协定》即将迎来10周年之际,今年10月,斯特恩撰写的《达成巴黎气候协定:如何实现、为何重要及未来展望》(Landing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How It Happened, Why It Matters, and What Comes Next)一书正式出版。他也在新书出版后第三次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
他在采访中详细回顾了自己在《巴黎协定》签署前那七年的工作与心路历程,以及所经历的中美气候谈判过程。他呼吁,人类正站在关键十字路口,2025年应当是各国制定新的国家自主贡献(NDC)、确立新目标的一年,面向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的关键节点,“我们应当全力以赴”。
澎湃新闻现将对话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抵达《巴黎协定》的道路
澎湃新闻:您为什么想要记录下这些故事?
斯特恩:因为《巴黎协定》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协议之一,也是过去百年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协议之一。
最初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可以追溯到1992年,但它非常宽泛,没有明确告诉各国具体该怎么做,并不是一项可操作的协议。制定一份可操作协议的努力从1995年柏林缔约方大会开始;但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未能发挥预期作用;2009年时,人们又寄希望于哥本哈根。各国20年来努力想达成一项协议,在巴黎终于取得了突破。我有幸站在了历史的中心,我想要记录下这段重要的历史。
澎湃新闻:回到《巴黎协定》之前,当时有哪些因素让您觉得《巴黎协定》是可以实现的?
斯特恩:首先,哥本哈根大会虽然很混乱,但它依旧有所进展。两页半的哥本哈根协议尽管未正式通过,但它微微削弱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防火墙”,使国际社会朝新的方向推进了一小步。2010年,国际社会花了一整年谈判,将哥本哈根协议的核心内容扩展至30页。随后的一年更重要,因为许多国家提出要开展更大规模的行动,最终我们在德班大会上建立了“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负责在2015年前形成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法律文件或法律成果,这为《巴黎协定》奠定了基础。
推动《巴黎协定》达成的另一关键因素是中美关系的变化。尤其是2014年两国进行了谈判,最终发表了联合声明,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两国各自的减排目标。声明虽然简短,但它不仅包括具体目标,还承诺两国将共同合作克服可能的障碍,这种合作精神具有重大意义。
澎湃新闻:在漫长、复杂的努力过程中,您是否曾感到过《巴黎协定》可能无法达成?
斯特恩:2009年时,我并没有从长远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当时,我们主要忙于处理已有的谈判议题,我们拼命跟上进度,与人们沟通,看哪些方法可行,哪些不可行,最终达成了类似哥本哈根协议的成果。
2011年之后,我们才真正看到未来的方向。此时,我们有了四年的窗口期,可以争取达成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协议。它需要具备足够的雄心,能够实现气候变化方面的关键任务。
2013年是个转折点,在当年的华沙缔约方会议上,各方就一些虽小但重要的条款达成了初步共识。2014年中美达成的协议向全世界传递了明确的信息:这一切正在真实地发生。这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积极影响。
长期以来,很多国家都在寻求一项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全面协议,因此我并不担心会一无所获,但我确实担心它内容有限——毕竟一项“协议”和一项“好的协议”之间差距很大。即使到了巴黎,我依然有疑虑。我担心一些国家可能会寻求简化的版本,可能只是规定一些透明机制,而将实质内容留待日后讨论。但随着谈判的推进,我逐渐变得乐观起来。
中美气候谈判:斡旋与友谊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当前的中美关系,特别是在气候变化方面?
斯特恩:我个人认为这种合作十分重要,我知道克里(美国前国务卿、首任美国总统气候特使)也支持中美气候合作,后来接替他的约翰·波德斯塔同样持这一立场。事实上,尽管中美在诸多领域关系紧张,但在气候变化方面,人们依然希望两国能够建设性地合作,延续巴黎气候大会的契约精神。
我第一次与解振华会面是在2009年3月,当时我对他说,我们可以将气候变化作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积极因素,甚至是“积极支柱”。尽管两国整体关系存在困难,我仍相信我们可以在气候问题上取得进展。他礼貌地倾听,但没有说是或不是。
2009年后,我们成为了越来越好的朋友,但中美气候合作进展并不明显。我记得2014年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准备会议上,我们十余人讨论了经济、国家安全、人权等问题,所有的讨论听起来都很紧张。在气候问题上,我们更是从来没有达成过共识。解振华和我都持同样的观点:中国想要X,而美国希望Y,X和Y完全不一样,要找到弥合差异的方法并不容易。
澎湃新闻:您说到了与解振华先生的友谊,这种关系对双边谈判有何帮助?
斯特恩:谈判人员首先必须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解振华需要关注中国的核心立场,我在美国也是一样。然而,如果两个人能彼此欣赏、信任并真正地倾听对方,尝试从对方的视角看问题,就更有可能找到平衡点。
一开始认识解振华先生,我就对他印象很好。他是一个有力量的人,也非常幽默开朗,总是乐观爱笑。我们刚开始时交流特别多,2009年我们见了六次,此后每年我们都见三四次,因为我们在为两国领导人的联合声明做准备,得经常碰头。
我记得有一次是在华盛顿,会前我们俩站在会议室里聊天,我讲了一个关于我两个孩子扎卡里(Zachary)和本(Ben)在车后座争吵的趣事。扎卡里想去面包店吃午餐,而本不愿意,最终扎卡里妥协了,但他提议晚餐要由他决定。本回答道:“我同意午餐,但晚餐我不认同。”我于是对妻子说:“本肯定是跟解振华学会了谈判技巧。”
解振华听完后哈哈大笑,他一旦觉得有趣或者愤怒的时候,脸就会泛红。他用中文回应我说:“不不,他是跟他爸爸学的!”这些细节很难准确描述,但有时候你就会有那种直觉,感到自己和对方很投缘。
澎湃新闻:这样的友谊在外交关系中常见吗?
斯特恩:这样的友谊不常见,但也不是闻所未闻。事实上,我在外交界确实有一些好朋友,不算多,其中一个就是解振华。
还有一次经历很有意义。2007年,我们正在和主要经济体论坛的17个成员国谈判一份联合声明,会议在意大利的拉奎拉举行,我们在前一天仍未敲定所有要素,基本内容虽已完成,但离正式协议还有一步之遥。当晚我们与各国气候部长开会,试图解决最后的分歧。
会议开始前,解振华把我叫到一个小房间,告诉我欧盟的一些国家正推动达成一项协议,目标是在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0%(现在我们已经在讨论2050年净零排放,但在当时,50%已经是非常大的跨步)。解振华对我说,中国已经做过测算,这一目标对中国而言会产生重大影响,无法同意这样的条款。我当时回答他:“那么我不会在会议上向你施压。”
我身边的很多人都说,你怎么能这么做?你应该对他施加压力,试图争取这个目标。然而,我认为那样做没有意义,我当然可以尽我所能向他施压,但他仍不会同意。这个对话发生得非常快,我出于本能地说,好,我不会追问这个问题了。我相信这对我们的关系更有益,对大局问题、中美关系更有利。
解振华事后多次跟我提起这件事,直到巴黎他都告诉我,这对他而言意义重大,意味着我在倾听他、试图理解他的立场。这不代表我放弃了美国的立场,而是尊重他的观点。
去年我在迪拜再次见到解振华,多年后的再次见面,我依然感到他是一个非常真诚善良的人。
全球气候行动的未来
澎湃新闻:您认为,美国大选后的领导人变化将如何影响全球气候治理?
斯特恩: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可能会让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他可能会大力支持化石燃料产业,特别是石油和煤炭的生产,这对全球气候行动将是极大的削弱。如果美国汽车公司因此而放弃电动车的研发,那么它们将在未来几年里失去全球市场份额。
我们正走在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上。若美国领导层坚定支持气候议题,会给全球带来一种积极的压力,比如奥巴马政府时期,领导人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将气候变化作为重要的外交优先事项;而特朗普再上台,其他国家可能会默认气候问题不会再在这些会议上被提及——因为特朗普甚至不觉得气候变化存在——这会极大削弱全球气候行动的能力。
好消息是,2016年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许多新的组织成立起来,比如“We Are Still In”,这个组织的成员横跨红蓝各州,包括许多商界领袖、政府官员和大学校长,表明他们仍然支持《巴黎协定》的目标。彭博社的创始人迈克·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和加州前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还进行了另一项努力,他们跟踪了各州、市政和水务公司等国家以下层面的减排工作,发现即便在缺乏联邦层面支持的情况下,依然有许多州和地方在努力实现减排目标。
此外,拜登总统的《通胀削减法案》(IRA)也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气候变化立法之一。该法案投入了数千亿美元的投资,其中许多直接流向了红州(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州),支持了当地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为民众带来了就业机会。即便有些人支持特朗普,他们也不愿失去工作。这些变化意味着气候行动不会因领导层的改变而停止,但如果有一位坚定支持气候议题的总统,这一努力将会更加强劲和有效。
澎湃新闻:您能谈谈对COP29大会上将要讨论的气候资金问题的看法吗?
斯特恩:今年的缔约方大会上,讨论的焦点之一将是资金问题。根据《巴黎协定》,发达国家承诺在2020年前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支持,虽然兑现得有些晚,但我认为在2023年终于达成了承诺。这一资金支持将持续到2024年,之后将设定新的目标,但资金量不会少于每年1000亿美元,这是双方商定的基础。
关于未来的资金需求,有些人认为每年需要1万亿甚至2万亿美元。这些数字并非毫无依据,因为如果全球要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包括提高抗灾能力、推动绿色革命以及其他真正能让我们走上正轨的工作,确实需要巨额资金。不过,这从未被纳入现有的谈判框架中。
我认为要从两个不同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一层面是重新确定1000亿美元之后的具体数字,可能会是1250亿、1500亿、甚至1750亿等,这是一个可控的范围。另一个更广泛的层面是几乎完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之外的资金改革,因为UNFCCC并没有直接的金融权力。
我们可以从过去几年G20的相关报告中了解可能的改革方向,尤其是去年秋天在印度G20会议上发布的《三重议程》报告,提出了对世界银行和多边开发银行的根本性改革建议,例如不仅要更多地利用财政能力发放贷款,还要利用这些资金降低私营部门投资的风险,以吸引私营部门资金来支持气候行动。
我希望COP29至少能在第一个层面上达成新的资金承诺,同时也推动与其他机构合作,以满足更高的全球需求。不过,我并非谈判代表,此次去巴库是应阿塞拜疆的邀请,参加国际顾问委员会的会议。
澎湃新闻:您如何回应那些认为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巴黎协定》所设定的气候目标的人?
斯特恩:我认为要实现1.5摄氏度的目标可能确实越来越难,但这仍然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如果无法达到,那么尽可能接近它也是有意义的,1.6摄氏度比1.7摄氏度好,1.7摄氏度比1.8摄氏度好。
尽管我们还没有完全走上正确的道路,但已有了显著进步,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和成本的快速下降,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如今,太阳能已经成为全球最便宜的电力来源,尤其是在非洲这类拥有极佳太阳能资源的地区。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在于政治意愿,特别是化石燃料行业往往推动政策向不利的方向发展,因为他们希望继续生产石油和天然气以获取利益。
2025年将是各国制定新的国家自主贡献(NDC)和新目标的一年,这对2035年之前的气候行动至关重要。如果到了2035年,我们仍未达成预期的减排效果,那么实现2050年的中期目标将更加困难。
(实习生刘卓尔、潘美竹对本文亦有贡献)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