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和政治思想往往是呼应时代的,因此,伴随着近年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政治极化的滋长和民粹主义(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自然而然会有不少学者将反思的焦点集中于西方的所谓自由主义体制,而仅在2023年,就笔者所见,即已有三种相关题材的新著问世,这未必直接宣告了西方自由主义体制的终结,却毫无疑问清晰地传达出其现正面临的巨大结构性、体系性问题。在2010年时,美国学者沃夫(Alan Wolfe)撰写了一部较有深度的《自由主义的未来之战》,在其中论调仍是自信满满,他宣称自由主义有七大倾向,即所谓“朝向成长,赞成平等,注重现实,考虑慎重,宽容为怀,欣赏开放,强调治理”,全是清一色的正向褒义词,他还信心十足地宣称:自由主义是“最适合我们这时代的政治哲学”,“自由主义的成功伴随着右派显而易见的衰退”,“自由主义成为现代政治中一个恼人的问题,原因并非它的失败而是它的成功”。这些话在2010年的美国背景下也许多少还有点道理,但放在2024年大选特朗普“前度刘郎今又来”的美国来看,则未免颇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
添加微信好友, 获取更多信息
复制微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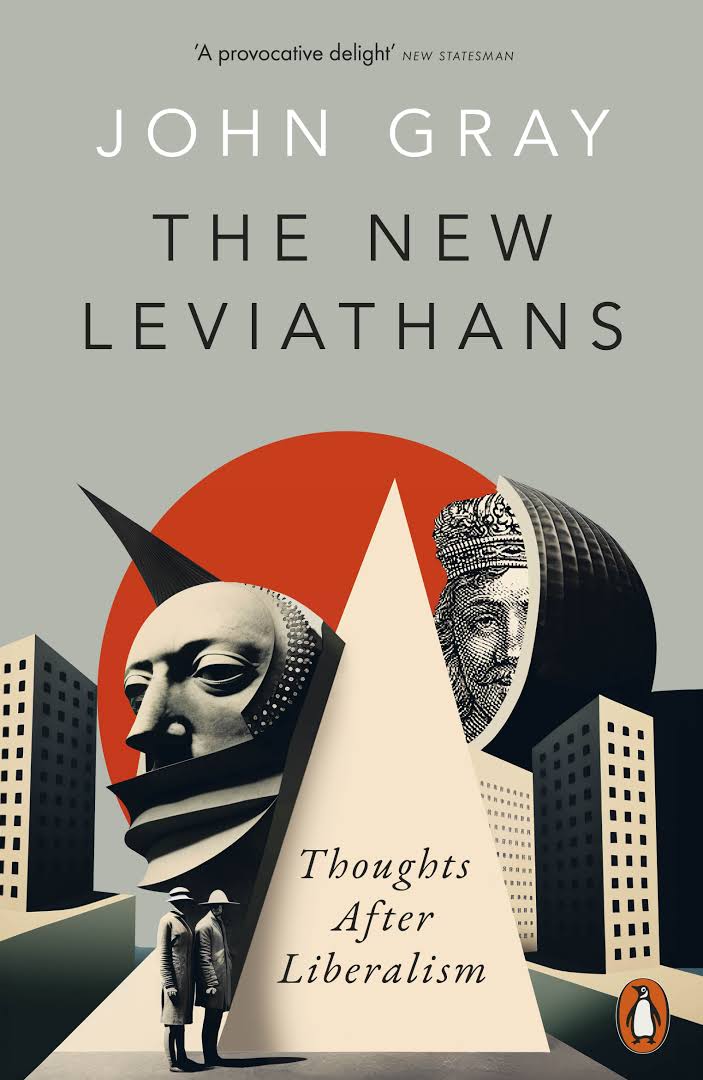
《新利维坦:自由主义之后的思考》英文书封
第一部书稿是伦敦政经学院荣休教授约翰·格雷(John Gray)所著的《新利维坦:自由主义之后的思考》(The New Leviathans: Thoughts After Liberalism)一书(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按照格雷的观点,苏联解体给西方带来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充斥着胜利主义情绪的时代:一时之间,生活在西方的人们发自内心地真正相信,一个理性、自由、治理有序的未来正在等待着人类去展开,而旧式的专横政治、民族主义和诸种缺乏合理性的因素已经成为过去。但事实是,从那时起,发生了那么多对西方而言可称是“可怕”的事件,那么多对西方而言可称是“有毒”的思想获得蓬勃发展,而西方的自由主义仍一味地确信无疑地将这些通通都视为“最终将会以某种方式被消解和祛除掉的一时反常现象”而已。面对这些“一时的反常现象”,西方的自由派们转而诉诸于身份政治等手段。按照格雷的看法,他们开始反对“养育他们的西方传统”,并在一场标榜“解构 ”(deconstruction)的狂欢中,号召所有人都切断与过去的联系,从头开始 “确定自己的身份认同”。格雷辛辣地讽刺到,尽管西方的自由派沉湎于他们所自诩的 "美德",但他们无法掩盖其自身不过是一群 “自我创造的偶像崇拜 ”的牺牲品而已。西方自由派想出的解决方案根本无力处理和解决手头急于星火的现实问题,对于政治极化所导致的政治效能降低态势也几乎视而不见。当年写下利维坦鸿篇巨制的霍布斯可绝对不会像他们这么天真,这么有自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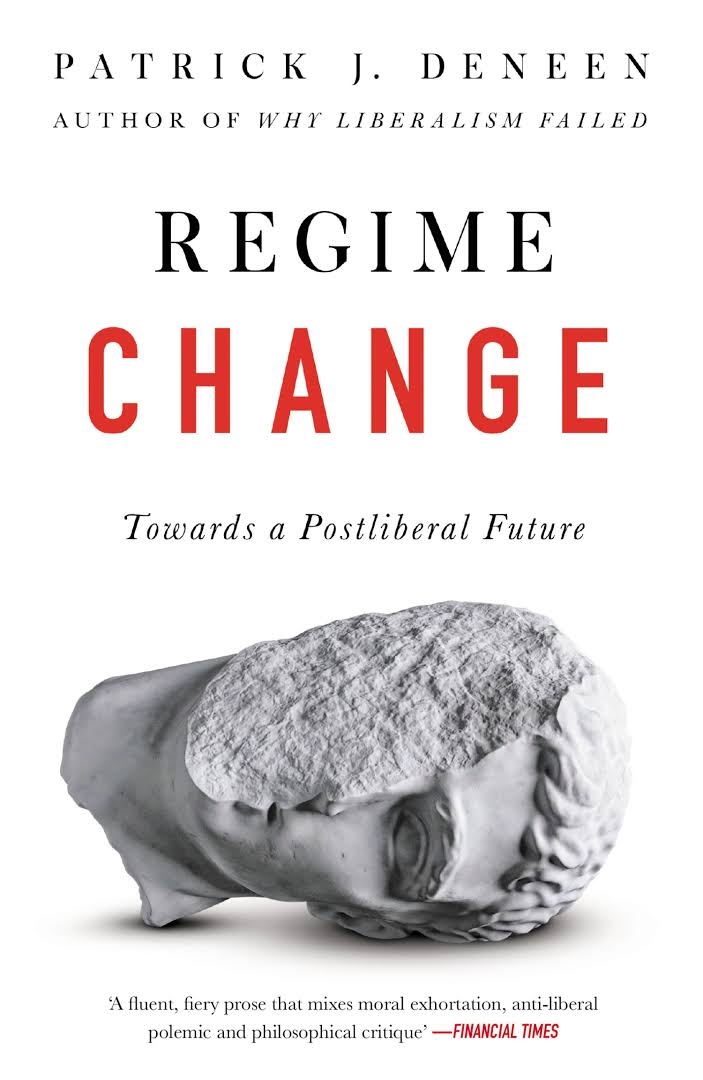
《政制更迭:迈向后自由主义的未来》英文书封
接下来将视野转到美国。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教授帕特里克·德尼恩(Patrick Deneen)于2023年出版的新书《政制更迭:迈向后自由主义的未来》(Regime Change: Toward a Postliberal Future,Sentinel出版社)和格雷的颇有相似相合之处(其旧著《自由主义为何失败》的中文译本已在2024年11月由新星出版社正式出版)。德尼恩认为,经典自由主义承诺推翻旧的贵族制度,建立起一种让个人可以创造自己的身份和未来的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做到了——但与此同时,它也摧毁了那些曾滋养培育过无数普通人的传统和制度,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具剥削性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所奉行的经济自由意志主义(economic libertarianism)、进步价值观和技术官僚范式的承诺,导致他们的统治常常会为了 “少数人 ”的利益而牺牲掉 “大多数人” 的利益,从而引发了西方当前的政治危机。针对此,德尼恩提出了一项较为激进的计划,以取代自由主义精英群体,和那种创造并赋予他们权力的意识形态。德尼恩认为,那些试图彻底摧毁统治阶层的草根民粹主义的努力是幼稚和不可靠的;西方当前需要的是战略性地组建一个致力于特定形态保守主义,并与“大多数人”利益相契合的新精英群体。他们会自上而下地努力形成一种新的执政哲学理念、执政精神风貌和执政引领阶层,最终可以将西方从一个只为所谓的“贤能之士”们服务的支离破碎的政治体制中转变与解脱出来。从具体政策面来说,德尼恩宣称自己所侧重的是人们的所谓“共同利益 ”(common good),在经济问题上,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名义上支持“与打工人们站在一起 ”的政策,加强工会组织,打击大企业垄断,限制移民数量。在社会议题上,德尼恩反对诸种有关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的进步主义范式的思想,支持促进异性恋家庭组成的政策。
至于德尼恩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则更是简单直白,他认为美国亟需一个能代表普通工薪阶层利益的政治保守派领导阶层,便能使各项问题都迎刃而解。德尼恩远非现实政治上的nobody, 事实上,他可算做是特朗普第二任期所择定的副手万斯背后极重要的意识形态策士之一,是当代美国民族保守主义(national conservatism)运动思想理论构造的极重要推手和塑造者之一。德尼恩与格雷一英一美,都身处学界,但其实这两人身上都带有鲜明的右翼阵营意识形态色彩,立论都是长期较为偏颇,抱持特定立场,不够客观中立。他们所讲(或者说,所致力于宣扬)的不少东西,其实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多年前就已在其《筑就我们的国家》一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中以更为公允、更为深刻和透彻的方式详细阐述过。而猛烈批判和抨击自由主义,也绝非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新事物,比如,早在1943年的《多余人的回忆》一书中,美国学者诺克(Albert Jay Nock)就曾毫不留情面地写道:“从1860年起,自由主义者就成为强制推行社会立法的主要力量。所有这一切,都在削弱社会的力量而增强国家的权力。借由此道,自由主义者们的表现好像若不废除所有的传统社会准则就誓不罢休。他们积极主张削弱个人自由,支持国家扩大其强制力的使用范围。他们的所作所为,说起来内容很简单,就是要使个体沦为国家奴役的对象,就是要塑造一个无比贪婪又横行无忌的集体主义怪物”(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译本,158页)。
相较而言,第三部关于自由主义存在问题的新著就要更为学理性和系统性一些,也相对更为客观和平正一些,这就是耶鲁大学教授,政治思想史专家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于2023年出版的《与自身作对的自由主义: 冷战知识分子与我们时代的形成》(Liberalism against Itself: Cold War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耶鲁大学出版社)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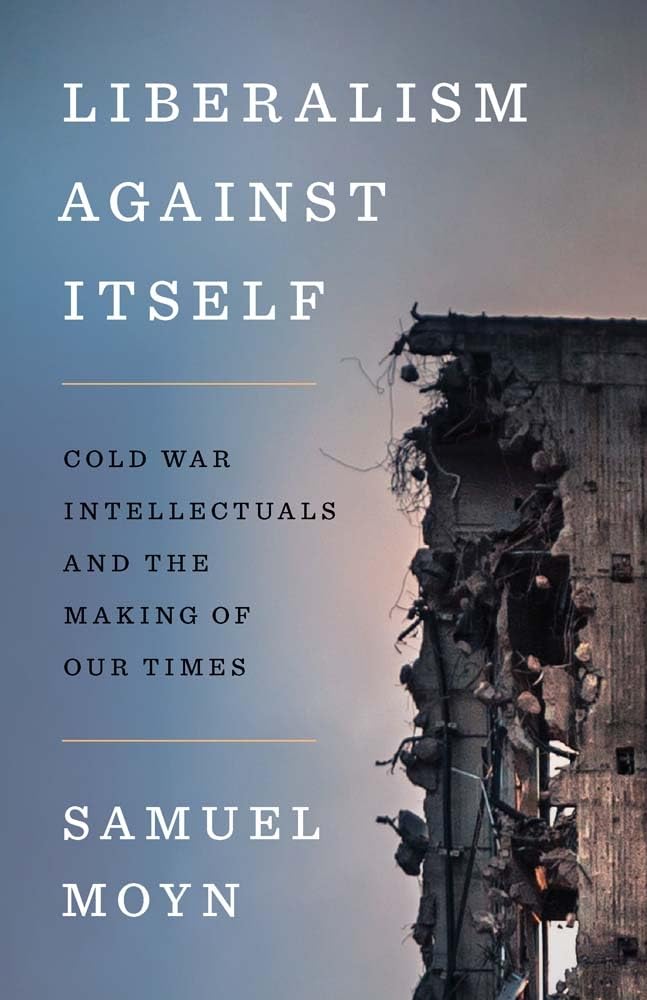
《与自身作对的自由主义: 冷战知识分子与我们时代的形成》英文书封
莫恩指出,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所面临的危机,其实有着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冷战起源。具体而言,在二十世纪中叶的时候,许多自由主义者对现代性所带来的世界局势感到黯然神伤:毁灭性的战争、日益兴起的所谓极权主义和长期存在的核恐怖。他们的结论是,西方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的旧理想,包括平等和解放等要素,非但没有为这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反而是制造和催生了这些问题。莫恩认为,冷战时期的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以赛亚·伯林、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卡尔·波普尔、朱迪斯·施克莱和莱昂内尔·特林(Lionel Trilling)等人——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由主义的样貌,为当今的时代留下了灾难性的遗产。莫恩向读者们集中展示了冷战时期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如何重新定义其运动的理念与理想,如何放弃启蒙运动的旧道德核心,转而追求一种更为危险的哲学:即所谓“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个人自由(preserving individual liberty at all costs)”。莫恩认为,冷战时期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乃是一种基于恐惧政治的假设——如果一个强大的安全型国家不能有效遏制世界上的敌对势力,那么自由体制就可能会崩坏为专制暴政。这种基于恐惧的假设其实和19世纪的经典西方自由主义理念恰恰背道而驰。莫恩明确谴责了这种立场和做法,同时也谴责了西方一些人近来将伯林式的冷战时期自由主义作为对抗非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手段的怀旧式情绪。在莫恩看来,及时建立起一种新的致力于解放和平等的自由哲学(emancipatory and egalitarian liberal philosophy)—— 才是一条可行的消除冷战破坏、确保真自由主义得以继续生存的道路。大约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到2024年,悉尼大学学者列斐伏尔(Alexandre Lefebvre)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as a Way of Life)一书,号召“自由主义可能是人们过上美好、有趣、有价值和有回报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通过更加认真地对待自由主义信仰,我们有可能成为一个更好、更幸福的人”时,莫恩就带头表示了明确的称赞与支持。
此外,法国思想史学者艾伦·卡汉(Alan S. Kahan)2023年的著作《免于恐惧的自由:一部不完整的自由主义史》(Freedom from Fear: An Incomplete History of Liberalism,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亦持与莫恩相近似的看法,在卡汉看来,一个规整严谨的自由主义框架至少应有两面,其中一面处理免于恐惧的问题,另一面则需使之能成为提供希望的源泉才行。自由主义观的论点通常要依赖于三大理论支柱:即自由、市场和道德,但如果自由主义观忽视了其中一个或多个支柱,那它们的论点通常就无法说服人。
其实,严格来讲,格雷,德尼恩与莫恩所攻击和批评的并不是完全的同一物,但其间确实存在许多重合之处。我们观察和分析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涨跌与起落时,未尝不应将这些新出的书籍作品一并考虑进去。
回到今日美国的场域,刚刚结束的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获胜本来就是可能性之一,不少预测机构都算是测准了(当然,也仍有许多号称专业的机构预测失准),但是很少有机构准确测算出特朗普能如此轻易地获得如此显著而巨大的胜利(笔者本人也完全没有意料到),在普选票方面都超过哈里斯500万张左右,成为共和党二十年来达此业绩水平第一人[1]。这里面的原因当然很多,比如有越来越多的各少数族裔背景的工薪阶层开始明确支持共和党,比如有不少评论者认为如无当时特朗普政府防疫大失败的背景拜登2020年本就未必能顺利选上,再如拜登政府一直无力结束俄乌与巴以持续延烧的武装冲突,又如民主党方面痴迷于身份认同的相关政治正确属性使普通选民离心离德等。但笔者想指出的是,我们也许不能机械、简单地将这场胜利看做一场所谓“乡巴佬对象牙塔” “野蛮蒙昧愚蠢对理性文明睿智” “下里巴人疯狂民粹对阳春白雪贤能智者”的胜利,因为至少在三个层面,共和党这一次都显示出了较为明确的智能方面的优势(或者说至少不落下风)。第一,单论学历,特朗普和万斯就显著高于哈里斯和蒂姆·沃尔兹(哈里斯所就读的法学院按照美国USNEWS国内法学院最新排名为全国第82名),第二,科技大亨马斯克的加持无疑为特朗普阵营方面加分不少,第三,由万斯等人操盘的所谓美国民族保守主义势力(natcon[2])早已将旧版的保守主义模式鸟枪换炮,升级再造,将其中引人非议甚多的新保守主义(neocon)元素和自由意志至上主义元素(或者说是新自由主义在保守右翼理念阵列中的投射)做了较为精细化的剔除,加入了更多的所谓“代表整个工薪阶层”的民粹路线元素,而放眼民主党方面,丝毫未见可以类比的举动。换句话说,如果民主党是今日美国政治场域中自由主义理念最强大的代表者的话,那么这种理念目前未必真就能占据智能层面的相对制高点,这也许是一个重大的深层结构性问题。当然,选战时期的智能未必直接就会转化为正式执政后的智能,特朗普第一任期应对疫情时的混乱无序处置以及其2021年1月间推动的强烈扰动美国宪政秩序的冲击国会山事件都仍历历在目,发人深省[3]。2024年大选成功打得美国政治自由主义毫无招架之力,固然令观者印象深刻,但政治自由主义是否从此灰头土脸,一蹶不振,隐入历史尘烟,则似乎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注释:
[1]参阅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elections/2024/11/06/2024-popular-vote-results/76088881007/
[2]参阅笔者: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232700
[3]参阅笔者: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449099
*本文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朱欣博士主持的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西方保守主义理论发展与困境研究”阶段性成果,基金编号24CZZ076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