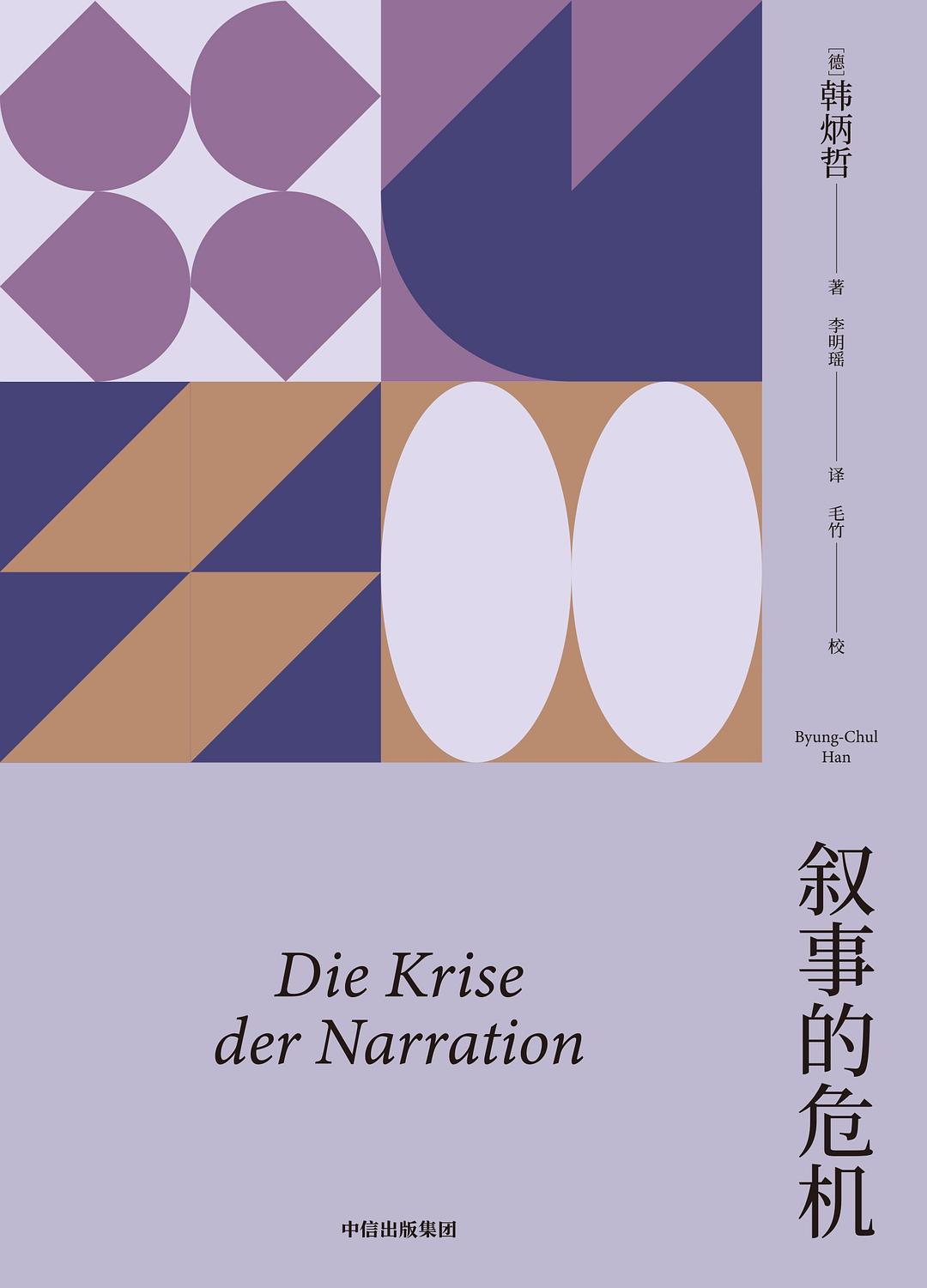
《叙事的危机》,[德]韩炳哲著,李明瑶译,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5月版,112页,48.00元
添加微信好友, 获取更多信息
复制微信号
德国学者韩炳哲(Byung-Chul Han)在《叙事的危机》(Die Krise der Narration,李明瑶译,中信出版社,2024年5月)的“前言”一开始就点出了该书的论述主题:“当今是一个人人都在谈论叙事的时代。矛盾的是,叙事话题的泛滥竟暴露了一场叙事的危机。在‘故事化’的喧嚣中,充斥着一种既无意义又无方向的叙事真空。”(第3页)作者在全书的论述中不断深入讨论的“叙事的危机”是双重的:信息时代造成的叙事的危机与故事化时代造成的叙事的危机,危机就产生于信息与故事化的时代趋势之中。
但是,在这本以“叙事的危机”为研究专题的著作中,作者并没有对何谓“叙事危机”下一个明确的概念性定义及阐释,我们当然不会钻进叙事学(narratology)的专业路径来追问比如“叙事与叙事结构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人们的知觉”所产生的“危机”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所谓“叙事的危机”当然不是现在才出现,韩炳哲在德国研究哲学、文学和天主教神学,他受到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关于叙事危机思想的深刻影响是并不奇怪的。在这部篇幅不长的论著中,他不断引述和阐释本雅明关于“讲故事的人”和世界的去魅化等议题的思想,叙事文学的死亡给本雅明所带来的个人震惊发展到韩炳哲这里,就成为了对时代病态的揭露和批判。当年本雅明面对的是复制技术和大众报刊的全面兴起,叙事文学的“光晕”(aura)逐步退隐;今天韩炳哲要呼吁的是反抗“叙事的危机”所带来的人类精神家园的沦丧。由此可以说,因意识到叙事的危机而产生的忧患感是比任何概念性的定义都更具有现实感的问题意识,概念化的阐释显然不是应对这个因信息泛滥和故事化而产生“叙事的危机”的最好策略。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韩炳哲的论述中的概念使用其实是有着不同语义的,当被翻译过来之后更容易在中文阅读中产生理解上的歧义。因此本书译者在“注释”中对韩炳哲使用的“故事”这个概念作了解释:“在本书中,‘故事’对应不同的德语单词,韩炳哲对此有所区分。Geschichte既有‘故事’也有‘历史’的含义,与Story相比更强调源初性,Story则更符合信息的特征,因此‘讲故事’(Geschichtenerzählen)是好过‘故事化’(Storytelling)的。Erzählung 意为‘讲述’,也有‘故事’的含义,从词源来看,erzählen有列举之义,更偏重与‘计算’(zählen)相对照。为避免造成混淆,本书中出现的Story,译者均使用加引号的‘故事’并加注原文。Erzählung多数情况译为‘讲述’,根据上下文有时也译作‘故事’。erzählen多译作‘讲故事’。译文无法体现德语单词内涵或可能造成混淆之处,均加注了原文。”(前言,第8页)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译者的处理是必需的。
在“前言”部分,韩炳哲对于“叙事的危机”的描述大体上是这样的:这是一个人人都在谈论叙事的时代,一个使叙事与讲述失去了生命的本真意义和凝聚力量的时代,也就是所谓的后叙事时代(postnarrative Zeit)。在后叙事时代中,叙事的魔力消失殆尽,讲述成为偶然的、可替换的、可变的,它不再有约束力和联结共同体的作用。有意思的是,作者把宗教叙事视作一种“具有内在真理时刻的独特叙事”:“基督教是一种元叙事,它囊括了生命的每个角落,并将其锚定在存在中。时间本身就具有叙事性。基督历让每一天都显现出意义。然而在后叙事时代,它被剥夺了叙事性,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日程表。宗教节日是一段叙事的亮点和高潮。没有故事,就没有节日和节日时间,也没有节日感,即程度更深的存在感,有的只是工作与休闲、生产与消费。”(同上,第4页)关于宗教的叙事性,在基督教视觉艺术传统中就有非常突出的表现,时间与事件的叙事性通过视觉图像而传达给信众的效果远胜于文字。在进入世俗化和后叙事时代之后,“节日被商业化,沦为事件和景观”(同上)。那么,进一步要区分的是“讲述”与“故事化”的本质差异:“讲述创造出共同体(Gemeinschaft),而故事化只催生出社群(Community)。社群是共同体的一种商品形式,由消费者组成。任何的故事化形式,都无法重新点燃那团把人聚在一起相互讲述故事的篝火。篝火早已熄灭。数字屏幕取代了篝火,将人当作消费者孤立开来。消费者是孤独的,不会形成共同体。社交平台上的‘故事’(Storys)同样无法消除叙事真空。那不过是色情的自我展现或个人广告。发帖、点赞和分享等消费主义行为加剧了叙事的危机。”(第5-6页)
应该说,一如韩炳哲被译成中译本的其他十几种著作,这部《叙事的危机》同样具有把哲学思考与写作文本贴近数字媒体时代的现实前沿、以哲学的人文传统和批判传统相结合、针对当下世界的精神状况展开论述的基本特征,他被媒体称为“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分析师”“大数据时代的哲学批判指南”是不无道理的。但是不知他自己是否意识到一个问题:他的著作在这个被他猛烈抨击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和讨喜点赞型社会中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和点赞,难道不会使他某些不乏思想性和批判力的论述被同化和被扭曲吗?看来作者并不担心成为“网红”,实际上愿意阅读和有能力理解一个来自本雅明和海德格尔精神家园的东方学者的论著的人毕竟是有限的。“叙事的危机”这样的“叙事”本身就是处于危机之中的警世之音。而在另一方面,作者对于确定和论述这个主题的必要性充满了信心:“信息海啸的冲击唤醒了人们对意义、同一性和方向性的需求,即要把让我们面临自我迷失的信息密林变得澄明。当前包括阴谋论在内的转瞬即逝的叙事和信息海啸,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身在信息和数据海洋之中的我们,在寻找叙事的锚地。”(第7页)无论“寻找叙事的锚地”的说法是否准确或深刻,那种在后真相时代的焦虑感的确要使人振作起来。
另外,也是如我读过的韩炳哲的其他几本著作一样,他的批判性总是指向西方社会的现实语境,无论是谈论“今日之痛”还是“叙事的危机”,都是指向从新自由主义兴盛年代到今天种种裂变危机中的西方社会,基本上没有触及仍然属于规训型和压制型的威权社会语境。关于“叙事的危机”的社会语境,同样指向了新自由主义:“在新自由主义制度下,共同体讲述明显已经崩解,成了自我实现模式的私人叙事。为了提高绩效和生产力,新自由主义将人孤立起来,阻碍了共同体讲述的形成,导致我们极度缺乏能够创造共同体和意义的讲述。私人叙事的过盛令共同体遭到侵蚀。社交网络上与自我展示别无二致的‘私人故事’严重破坏了政治的公众性(Öffentlichkeit),给共同体讲述的形成增加了困难。纯粹意义上的政治行动以叙事为前提,也就是说,它必须是可讲述的。没有叙事,行动就会退化为任意的行动或反应。”(82页)这是在阅读韩炳哲关于当下世界的批判性论述的时候必须注意的语境问题。当他说“这种叙事危机由来已久,本书将对此寻根探源”(前言,第8页)的时候,我们同样应该对他所论述的危机及其来源的具体语境有明确的认识。
上述这两个问题看起来都不是他的责任,但是对于不同语境中的读者来说,不能不意识到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他在《妥协社会:今日之痛》(吴琼译,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指出当下世界最流行的是右翼民粹主义和专制主义,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自由主义,而是来自极权主义与数字监视技术的结合,使人们正在面对的是“一种生命政治的监视政权”(71页)。这可以看作是韩炳哲思想光谱中的一种基本倾向,但是《叙事的危机》却基本上没有涉及这样的观察与批判视角。本来在涉及信息传播、言论表达、讲述的权力与权利、共同体的组成原则等议题的时候,关于什么是“叙事的危机”的“最大危险”、其最具有侵蚀性的“来源”又究竟在哪里等问题应该是不容回避的。
我们从作者的论述中选取一段来讨论:“资本主义借助故事化将讲述占为己有。它让讲述听命于消费。故事化生产出消费形式的故事。在故事化的帮助下,产品被赋予了情绪,向消费者承诺独特的体验。如此一来,我们买卖、消费的其实是叙事与情绪。‘故事’被推销,故事化实为卖故事(Storyselling)。讲述与信息截然对立。信息强化偶然性经验,而讲述则将随机性转化为必然性,从而减少偶然性经验。信息没有存在的强度。……因此,存在的缺失,对存在的遗忘,是信息社会所固有的。信息只能进行叠加和累积,不承载意义。讲述才是意义的载体。意义原本是指方向。我们今天确实接触到异常丰富的信息,但却迷失了方向。”(前言,第6页)这是作者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的“信息”与“讲述”的观察与批判,在一些介绍和评述该书的文章中也是常被引用的。在这里,对于消费社会中的信息与讲述的论述对于我们颇有启发性,但是由于语境的不同,或许更应该思考的是从韩炳哲的版本转化而来的另一种论述:规训的权力借助故事化将讲述与故事占为己有,让讲述与故事听命于规训权力;必须要使讲述与信息高度统一,以信息强化讲述,并将讲述中的偶然性裁定为必然性;信息的叠加和累积只能是同质、同源的,所承载的只能是被许诺的意义;人们确实可以接触到被允许的异常丰富的信息,从而只知道一个被许诺的方向。
实际上,当韩炳哲偶然论述到哲学与学院的时候,版本的转换也就自然出现了:“一旦哲学以科学自居,甚或以一门精确的科学自居时,它的颓败就开始了,因为它否定了自身原有的讲述意味,于是失去了自己的语言,陷入了缄默。学院式哲学不遗余力地‘管理’着哲学史,这样的哲学是无法进行讲述的。它根本不是冒险行动,反而成了个官僚机构。面对当下这场叙事危机,哲学领域也没能幸免于难,正面临着终结的威胁。我们已经不再敢于面对哲学,面对理论,自然也就失去了讲述的勇气。”(68-69页)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韩炳哲从“叙事的危机”视角转向了哲学的危机的视角,提出的是关于危机的叙事的问题——当哲学力图具有官僚机构的权威的时候,它的最大危机也就降临了;如何讲述这样的危机,显然就有了重新回到真正的叙事与讲述的必要性。
关于“讲故事”,这是从本雅明延伸到韩炳哲的一个重要议题。“如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少讲故事(Geschichten)。信息交流成为交际方式,使讲故事严重受阻。社交平台上也鲜少有人讲述故事。故事通过提升共情能力将人们彼此联结。故事创造出共同体。智能手机时代共情的丧失充分说明,智能手机并不是一种讲故事的媒介。”(第7页)“社交网络上的‘故事’(Storys)实际上不过是令人陷入孤立的自我展现。与讲述相反,它们既不产生近端,也不催生共情。归根结底,它们是视觉上被修饰过的信息,被接收之后便会迅速消失;它们不讲故事,只做广告。追求关注并不能创造共同体。在故事化即卖故事的时代,讲述和广告难分彼此。这就是当前的叙事危机。”(77页)把“讲故事”作为人类交往和建立认同感的基本方式,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当下时代是否越来越少讲故事以及需要讲的是什么故事,一方面既依赖于对什么是“故事”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不同社会语境中关于“讲故事”的空间问题。
在“讲故事”这个议题上,韩炳哲没有像在谈到政治行动与叙事的关系的时候那样引述汉娜·阿伦特的思想,进而把“讲故事”的语境和意义延伸到它更应该去往的地方,这是令人感到有点遗憾的。因为韩炳哲所引述的阿伦特把政治行动与叙事看作是“总能形成一个故事”的论述中,实际上已经触及了阿伦特关于“讲故事”的重要思想。与政治和自由相联系的是重视“讲故事”(story-telling),这是阿伦特的重要思想特质。她始终认为人类经验的独特性与多样性难以在传统的哲学表述方式中得到表现,只有在“讲故事”的文学资源中得以实现。她特别指出,试图用“专制”这一古典政治概念来理解极权主义,将不可避免地有扭曲这一现象的极端新颖性的危险,从现存的理论和哲学体系出发来对它们加以说明变得极为困难(西蒙·斯威夫特 《导读阿伦特》,陈高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页) 。应该说,阿伦特对“讲故事”的重视与她所要处理的念兹在兹的那个核心论题——揭示历史创伤和抵抗现实政治的罪恶——紧密相关。西蒙·斯威夫特以意大利作家普莱默·莱维(Primo Levi,1919-1987)在回忆录中讲述自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与一位同屋囚犯的谈话为例,作为对阿伦特的“讲故事”的“导读”。斯威夫特认为,若对莱维的故事进行抽象性的讲述,就难以想象所获得的意义还具有同样的力度;甚至做任何简单的解读都会损害故事的复杂性和微妙之处。 这就是阿伦特“讲故事”的真谛:你无法把谈论政治的阿伦特与讲故事的阿伦特分隔开来。面对史无前例地残暴、新颖、独特和复杂的纳粹极权主义,她不相信单凭概念、定义和推理的法则就能把它揭示出来和表述清楚;即便是在对纳粹分子的审判中,她也无法完全相信司法体系的合法性与智性,而宁愿相信记者、诗人和历史学家——历史学的古老语义正是“讲故事”,阿伦特是在面向生命体验、政治与真理、历史与创伤的层面上肯定“讲故事”的文学家与诗人。在阿伦特之后,捷克著名剧作家、政治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对 “讲故事”也作出了深刻的论述,他指出有一种制度“在本质上(和其原则上)是敌视故事的”。他在监狱里发现几乎每一个囚徒都有独一无二的、令人震撼或激动的生活故事,哲学故事以证明了一种叛逆:独特的人性用叛逆来抵抗它自身的虚无化;并且用自身具有的顽强精神来无视消极性的压力。在他看来讲故事就是抵抗威权统治的有力武器,因此必须讲述那些故事——那些处于危机中的人类命运的故事。
应该说,韩炳哲关于讲故事的论述仍然具有某种现实批判性意义:“现在连政客都懂得贩卖故事的重要性。……叙事就这样被政治工具化了。问题的重点不再是理智,而是情绪。故事化作为有效的政治交际技巧,绝不属于那种面向未来、给予人们意义和方向的政治愿景。政治叙事的意义在于承诺事物的新秩序,描绘可能的世界。如今我们缺失的正是给我们带来希望的未来叙事。我们在各种危机间转场。政治削减成解决问题。唯有讲述方能开启未来。”以“讲述”作为开启未来的唯一途径,因为“讲述具有‘重新开始’的力量。任何改变世界的行动都以讲述为前提” (87页)。这也只能从韩炳哲关于“生活即讲述。人作为一种叙事动物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够通过讲述实现新的生活方式”的论述来理解。
在全书最后,韩炳哲实际上是讲述了一种关于危机的叙事:“在故事化的世界里,一切皆沦为消费,导致我们对别样的讲述、别样的生活方式、别样的感知和现实视而不见。这就是故事化时代的叙事危机。”(同上)这里的关键就是如何克服对于“别样的讲述、别样的生活方式、别样的感知和现实”的遮蔽,以及如何讲述那些故事。

柏林欧洲被害犹太人紀念碑 纸本彩墨 李公明 作 2024年11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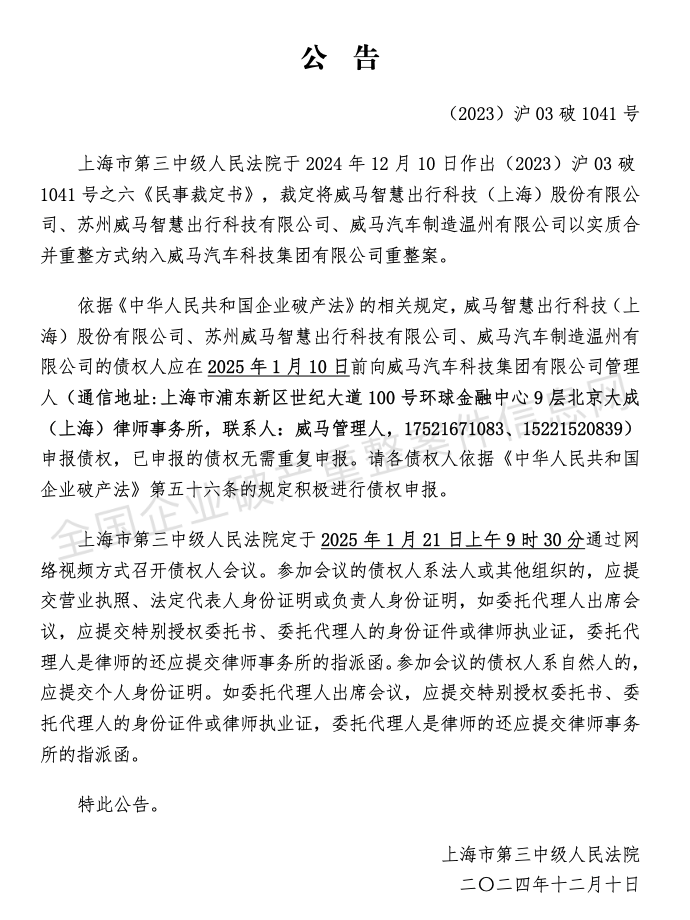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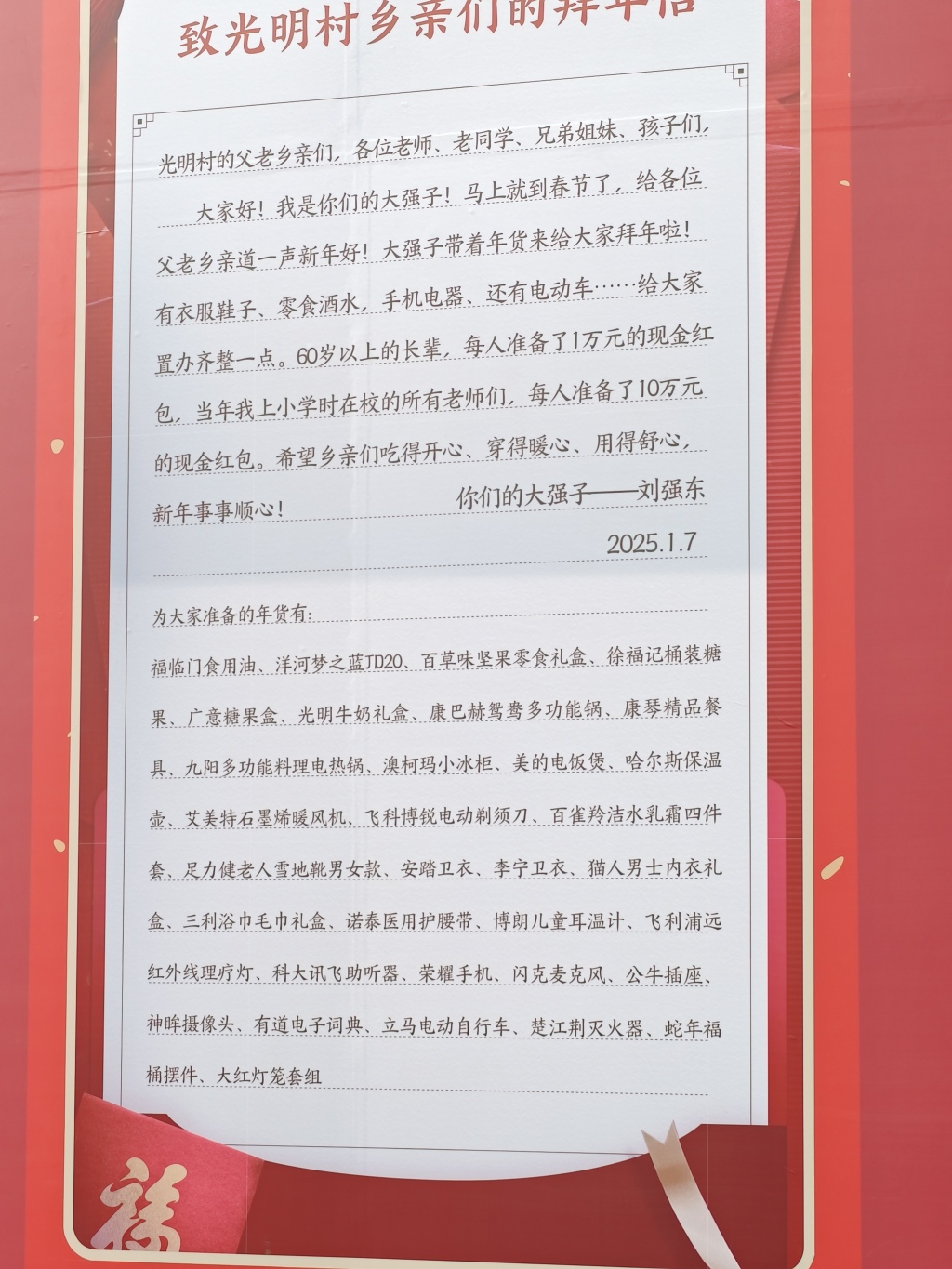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